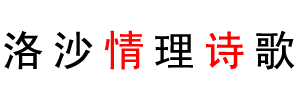老家的屋檐下有一块大青石,就摆放在大门的右侧。这是一块普通的河滩上的大青石,高半米,长不足一米,大致呈长方体,顶端还算平整,底部一侧稍有悬空,但依然稳实。它青里泛黄,光滑宁静,已说不清是怎么来到屋檐下的,爷爷奶奶活着时经常坐在上面,父亲母亲也常常坐在上面。 老房子已没有人住了,听厌了城里的吵杂,偶尔一家人回来,妻子收拾床呀、灶呀,我必首先擦洗大青石,端一盆水慢慢还原往日的记忆。石沿上有一处凹陷,呈黑色,那是爷爷抽烟的烟锅儿敲打的,旁边凹陷下去那部分,那是母亲年复一年浆洗床单被褥时磨下的,底部那块黑色是我小时候放鞭炮被火硝烧的,垫在墙边的小石头还在,那是父亲平日里坐在大青石上破柴时做垫石的。岁月沧桑,物是人非,而大青石依旧静卧在屋檐下。 我清晰的记得,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父母亲从地里背着粮食回来,不管夜有多深,爷爷就坐在屋檐下的大青石上等候。漆黑的夜里,静寂孤寞,爷爷一锅接一锅抽烟,每吸一口烟的光点,很远就能看到,那就是希望。父母到家了,也不用呼喊,一声咳嗽,爷爷就知道家人回来了,赶快到屋场边迎接。 奶奶活着的时候,老见坐在大青石上纳鞋底,说是纳鞋底,其实眼睛早就花了,但毕竟是个活计,谁路过场边,奶奶就拉着坐在旁边的木凳上,家常一唠就是半天,留下的半拉子“工程”还得母亲收拾。奶奶特喜欢大青石,每个夏天几乎就是坐在大青石上度过的,父母曾担心石头太凉,奶奶却说:“没事,坐在上面心里凉凉儿的,把心里的火气坐没了,胜过吃药打针,比孙子的空调都强多了。”奶奶一直活到84岁,大青石成了她的高档“家具”。 我记得,秋夜里,明月高悬,母亲坐在大青石上,旁边放一个笸篮,家人围着剥玉米棒子的情景。虽说母亲劳作了一天非常辛苦,饿怕了的她把粮食看得比啥都重要,有玉米剥那就是最幸福的事,也是最享受的事。母亲总是一边剥玉米,一边滔滔不绝地讲她那陈旧的古经,直到夜深。 我还记得,在大青石上打糍粑的事。土豆蒸熟了,得趁热将土豆皮剥下,全家人围在锅边,一人一个小盆,看谁先将盆儿剥满。然后洗净大青石,开始轧剥过皮的土豆,最初的总是由我来轧,慢慢地土豆泥越来越多,越来越粘,木锤上粘得满满的,轧不动了就由爷爷轧,爷爷轧不动了,就由父亲轧,母亲则在厨房里烧酸菜浆水。家里的糍粑劲道耐嚼,一连吃好几天也不觉得厌。 农村除了过年过节,吃饭几乎不坐桌子,平常吃饭一人端一个老碗都集中在大门外,长辈坐在大青石上,其他人围着大青石随便拉个小凳子坐下,还有的直接坐在大门的门槛上,那种情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畅快、乐哉! 前些天邻居盖新房,说是房根基还差一块大石头,想把屋檐下的大青石拉去,我坚决不同意,家里老人一个个去世了,如果大青石不见了,那老家还有啥让我念想的呢? 大青石既是老房子的镇宅石,又是聚财石、和气石,更是我心中的神石,沉沉甸甸的,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