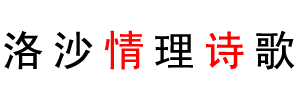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罗凤霜 于 2018-6-25 22:15 编辑

我 “爹”
文字:罗凤霜
在六七十年代,我们村建成国防厂了,村子被厂区重重包围着。工人大都来自北京,他们的孩子就在我们农村学校和我们一起念书。工人子弟不仅穿的漂亮,特别是都会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而我们村里人却是拉着老长的“湖广广”话。比如,普通话叫“母鸡”“公鸡”“小孩”“鞋子”我们却要用近似四川话的腔调叫“鸡母”“鸡公”“娃儿”“孩子”这样叫着,难免就惹得工人子弟同学们一阵哄堂大笑。
特别让我难为情的是,村里的小孩子都赶时髦,也随工人孩子管父亲称“爸爸”,可我家却硬要让我们管父亲叫“爹”。当时,我们这样的称谓,就显得有些另类,总遭到我的那些工人子弟同学们地嘲笑。每当这时,我就觉得叫爹太丢人,总不愿意在广庭大众之下大声好好地叫一声“爹”,还暗暗地抱怨他真是老土,给我们丢尽了面子。
记得,我在公社“五七”学校读小学五年级时,那时是寄宿制,每位学生每学期要交300斤柴火,才可以在学生灶上打饭吃。
一次,我爹背着一大背架柴火,跋山涉水,大汗淋漓地来学校给我交柴火,可我却不顾爹跑了十几里山路的艰辛,当一伙调皮同学阴阳怪气地嘲笑我管父亲叫爹时,我竟然连大声叫他一声“爹”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对他说:“你来了,我去给你打玉米糁子吃去!”
我爹知道我对他的排斥和不满。可他却没责怪我,只是说:"我不累,也不饿。"当他知道我们班同学都买了一本必备的字典时,他二话没说,就把给他买雨鞋的钱给我也买了一本比他们还好的字典,然后,他默默离开了学校。
那时,爹在队里管水泵排水灌溉田地的任务。每天都在冷水里泡十几个小时,因此,他得了关节炎,每到阴雨天,他就腿脚疼,可我爹为了我买字典,却放弃为自己买雨鞋.
当我目送着他远去的背影时,发现我爹替我背柴火时,脊背被柴火划破的一道大口子上一大片汗渍紧紧地贴在他勒的红肿的肩膀和背上的血口上,浸出一大片殷红的血渍.还有,他前不久为救村里小牛犊而摔伤的那条一瘸一拐的腿,顿时,我止不住的泪水从眼眶夺眶而出。我一遍一遍地抱怨起自己,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啊,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于是,我边哭边追着我爹,大声喊着“爹-爹-爹-”我爹在老远听见我喊他,回过头朝我笑了笑,把手挥了挥说“回去吧!好好学习!”从此,我再也没嫌弃叫“爹”老土了,感到叫“爹”是自豪的。

其实,我爹他有个很儒雅的名字——罗朝卿。他高大,魁梧,一张清瘦英俊的脸颊,他那双深邃的眼眸充满了智慧,他知书达理,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算盘也打的顶呱呱,是那时村里数一数二的文化人,当地十里八村哪家遇到麻烦事,都会找我爹商量,讨个好法子。只见那些找他的人,个个来时一脸愁云,可经我爹一说道,事情就会化解,走时,那一脸的茫然、疑云散尽,因此,在社教期间,我爹被抽去乡工作组住队,当然他每天要干的工作就是写写画画,下乡进村解决社员间一些琐碎棘手的问题。本来,我爹干这差事是得心应手的,常常把工作做得停停当当,领导很满意。
“可是,那份差事,挣钱少,一家人缺口粮,老饿着咋办?我不能让娃儿们受罪呀!”我爹对我母亲说。
我爹为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不饿肚子, 他果断辞掉乡里工作组的差事,丢下手中的那只笔,回乡拿起了锄把、镰刀、驾起了牛,用铧犁地。从此,我爹就成了一名真正的庄稼汉。
我爹每日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下地干活,一年365天从没请一天病假。天晴,他给生产队犁地;雨天,他给生产队放牛、算账。
夏天来了,他每天早早起床磨刀,然后,喝点茶,吃点玉米面馍馍,就背着背架子去生产收麦子去了。
蔚蓝的天空,一轮烈烈的艳阳下,一望无际的麦浪翻卷着,起起伏伏如金色的波浪,我爹手拿镰刀,赤膊下地割着麦子。只见他左手拢一把麦秆,刀口在麦子根部轻轻一划,随着“咔嚓嚓,咔嚓嚓”几下脆响声,麦子已齐刷刷齐根割下,倒在地上,他一会儿割,一会一捆。我爹两手配合协调,动作敏捷,是那样娴熟、优雅,在如火炉般热烘烘的天地间,他正挥舞着银光闪闪,亮亮铮铮的麦镰,演奏着一曲夏日欢快劳动的高亢华章!
我和弟弟妹妹随老师一起在他们身后捡麦穗,不时就瞅见我爹时而直挺腰杆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额头的汗水,时而俯身割麦,一次又一次的弯腰,重复着那已做过千万次的动作。猛然间,我抬头看见,我爹草帽下的那张脸不再是当年的白皙英气,而是,一张爬满皱纹的,历经沧桑的红黑色的脸膛上却布满了收获的喜悦,或许是因为他的辛劳能换来我们全家人的口粮,还能交付起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的学费钱。
晚上,劳动了一天的爹,他吃了一个玉米面发糕,喝了一碗面汤,就靠在草垛上眯着眼休息一下,随着打麦机的轰隆隆响声,他就又参加到打麦子的洪流中,他主要负责摞麦草垛的任务,这可是个技术活,必须把麦草垛摞的四方四正,结实稳固,既使遇到连雨天,也不进水;如摞不好,麦草垛子遇到雨易灌水,麦草就会窝烂发霉,生产队的牛就没有了草料可吃。因此,这差事,就自然落到我爹的头上。我爹摞起麦垛来动作娴熟,麦叉子在他的手中一起一伏,一上一下跳着,那招式都和下面甩麦草的大叔配合的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我爹摞起的麦垛有方有圆,不仅结实漂亮,从不进水,保管能管到第二年开春牛有草料吃。
秋天来了,我爹和队里的一位大叔又扛着犁铧,赶着牛上山犁地播种小麦去了。他先把一袋子的麦种子倒在大筐里掺和上化肥,再提着竹篮子,一大把一大把的将麦种均匀地撒在那块要耕种的地里,然后,驾牛来回不停地犁地播种小麦。
一铧铧过后,黑色的泥土在我爹的犁铧下翻起了泥浪,一粒粒麦子便安然躺进了犁铧沟里,等待着发芽,破土而出,来年又有一片金黄翻滚的麦浪等待村民收割。
我爹就是这样在生产队的土地上经历着千万次的鞠躬倾倒、顶礼膜拜中,收获了一年又一年的期盼。
我爹他是农民,用一辈子弯腰躬耕,才换来了我们兄弟姐妹们衣食无忧,圆了我们读小学、上高中,念大学的梦想。
1981年9月我踏上离家的路,考上距村子60里以外的留凤关高中时,我爹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为,我是当时我村那年唯一考上高中的一个女孩子,他不住地告诉我:雨天别一个人回家,要结伴而行,万一雨大回不了家,就住在学校里,他会抽空送给我粮食。
当我挥手与他告别的一瞬间,我瞥见他黯然浑浊的目光有泪痕滑落。原来,我爹是想起我高考结束回家的路途遇到倾盆大雨,山洪冲倒公路两旁的楼房,我差点被波涛汹涌的洪水卷走的事情。
我爹,就是这样默默地关注着我,牵挂和念叨着我。在他眼里,我是始终都长不大的需要他照顾、呵护的女儿。他用无私的绵绵不绝的爱和无尽的亲情为我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让我幸福的度过每一天。
1994年我要参加大学自考,我老公不想让我熬更守夜苦读,他说他能养起我和孩子。当我爹知道我的想法没有报名费时,他把自己看病的200元钱硬塞到我的手里,和母亲帮我在家带孩子,支持我从甘肃茨坝坐火车去凤县城报名。在我爹的支持鼓励下,我勤奋学习,刻苦攻读,终于不辜负爹的期望。完成了自考的所有课程,拿上了红红的大学毕业证书。
现在,我有了一份衣食无忧的工作,可以孝敬爹他老人家了,可是,他却突发心脏病,默默地离开了我们。当我得知噩耗,回家时,他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我撕心裂肺,嚎啕大哭,扑上前喊着:“爹!爹!您怎能丢下我们呢?你怎么不等让女儿再看看您一眼呢?”可是,我爹,他依旧紧闭双眼,安详的永远这样“睡着了”。
从此,每个静夜,我会独思爹爹,眼前时时浮现出他为我送柴火的一幕.特别是他在田间弯腰割麦的样子和他犁地撒麦种时挥汗如雨,躬腰身影劳作的身影。
我爹虽是一个极普通,很平凡的乡下老农民,但他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为我们每一个儿女铺平生活和学习的道路,他的举手投足和音容笑貌我将一生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