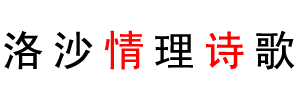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红米饭 于 2015-2-28 10:52 编辑
(图片来自网络)
油灯情怀 文/天涯碧草
大巴车驶进那古老典朴的村庄,停靠在村口空旷的麦场上,从车上走下来,村道两旁的建筑呈现着关中地区特有的风格,庭院门口的树木在微风中摇曳着枝条向来往的行人热情招手。 走进院落,脚踏青砖,眼瞅着“斑驳”的墙壁,看着古老的厦房里的陈设,那一铺暖炕似乎还残留着温热,炕头靠门的地方是泥、砖做成的盛物台,上面摆放着一盏油灯。心里猛然一热,多久了?在记忆的脑海中搜寻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渭北高原一个不起眼的村落。那时,村里还没有电,家家户户照明的工具就是煤油灯,在漆黑的夜里摇曳着的微弱的光芒。那如萤火虫般的光,给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带来一丝光亮,也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油灯,是村子里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家境好一点的人家,用的是透明的玻璃罩子灯,油灯的身子里装上煤油就可以点燃,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可以调节灯光大小的机关。玻璃罩子罩在点燃的灯捻上,火光顺着一个方向,围在旁边的人就不至于将鼻子熏黑;一般人家,都是用孩子用过的空墨水瓶或者从药店讨来半透明玻璃瓶,装上煤油,给瓶盖上扎一洞,再用棉线搓成比较粗的捻子,穿过瓶盖上的洞,大半留在瓶子里浸在煤油里,等浸过油后慢慢地燃烧。夜色降临,要得等到屋子完全看不见的时候,才可以点上灯,一家人在灯下各自忙着。 母亲是一家的主要劳力,除了白天在生产队劳作之外,晚上还要在油灯下纳鞋底、缝衣裳,纺线织布,全家六七口人一年到头的穿穿戴戴就在这昏黄的灯光下由母亲勤恳地做着。 冬日的夜格外长,夕阳还没有完全落下,油灯就被点燃放在炕头的砖台阶上,油灯的一边是奶奶坐在温热的炕头有节奏地摇着纺车,棉条在手的摇晃中被抽成细细的棉线绕在锭子上,纺车嗡嗡作响。另一边是地上的母亲坐在织布机上双脚踩着踏板,两手交错着梭子来回穿梭。纺车的嗡嗡声,啪啦啪啦的机杵声交织着,就像一首轻轻的歌谣回荡在我们的耳边,伴着年幼的我们进入梦香。 印象最深的、最快乐的还是每每临近春节,母亲除了给一家人准备新衣服、新鞋子外,还会拿出藏在箱底的剪纸样子和祖父从集市上带回来的彩纸。精心地剪出窗花增加年的喜庆,这时平日里和蔼的母亲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嘴里还哼着听不清楚的小曲。哥哥忙着做自己的假期作业,我和妹妹就可以紧紧地盯着母亲,看她将剪纸的样子贴在彩色的纸上,然后在油灯上熏,火候非常有讲究,容不得我们碰一下母亲的身子或胳膊。不然就会遭来白眼甚至被训去睡觉,那是最扫兴的。所以我和妹妹就静静地坐在离母亲稍微远一点但还要能看见的地方。大气也不敢出的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唯恐错过了一个细节。有时也会在大白天里躲在大人们找不着的地方,偷偷点上油灯,模仿母亲熏窗花、剪窗花,拙手拙脚的向小朋友们卖弄。 母亲剪出的窗花有十二生肖,有吉庆有余等。剪好的窗花由父亲在除夕那天和哥哥一起张贴在窗户上的。第二天各种小动物在红色的油光纸上,迎着节日里初升的阳光,个个栩栩如生。还会剪一些秦腔剧目里的人物,最多的是“三娘教子”,是用黑色的油光纸剪出来的,一般贴在窗棂格的中央。 岁月如歌,春夏秋冬,在油灯微弱昏黄的光芒中我们一天天长大。记得到了七八岁的时候,若是家里没有煤油了,就会让我带上角票去邻村的供销社去买一些回来。我喜欢看供销社的叔叔或者阿姨拿起一个长把的勺子伸进装煤油的大缸里,舀上一勺,顺着漏斗灌进我带来的瓶子里,听着哗啦哗啦的声音,闻着煤油的气味,心里有一种别样的快乐——我长大了。 差不多到了八十年代初,村子里通上电,各式的煤油灯就被主人收了起来,有的甚至像扔废旧物一样丢掉了。细心的父亲却把油灯收在家里窑洞的最深处,以备停电时候急用,有时也成了我们偶尔拿出来玩的物品。 过去的日子就像东流水一样一去不返,可童年里的油灯却永远留在了记忆中。在煤油灯下,我懵懵懂懂体会到了长辈的辛苦,更多的是品尝到了亲情的温暖。 如今,只能在博物馆或者一些农家乐看到煤油灯,看着满是沧桑的油灯,母亲忙碌的身影,奶奶摇着纺车的歌谣,兄妹们读书、嬉戏的情景就在眼前浮现,是呀,时代落下的印记,只能成为记忆,只会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再现,那是一种无法用文字表述的情愫。 煤油灯,一次次感动着我,一次次将我带回儿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