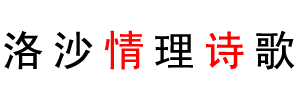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魂归黄土地
父亲去年八十六,今年八十五。不是我被生活折磨得颠三倒四——算不清数儿了,实是民间有一个说法:“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叫去商量事。”所以这个岁数上的老人都比较忌讳。去年初父亲曾说:“天赠一年,地加一岁。我今年八十六了。”老人不糊涂,这不是账算问题! “越活越年轻”的父亲其实是无法抗拒万物都要衰老的自然规律,自从八年前秋季的一天后晌在院子锯木头,因用力过猛,摔了一个仰背,细肠撕裂,内脏出血,生命从悬崖边上被挽救回来后,先前每顿吃几老碗扯面、几个蒸馍,抡鐝头左右开弓,骑摩托风驰电掣的壮汉就变得萎靡了。老风湿、高血压、冠心病等等也乘虚而入。这几年,父亲的病越来越复杂,他的身体就像一个碌碡在慢慢坡上往下滚,越滚越急,越滚越快,即使成天吃药、打针,每年住几次院,也难治疗他的病,如今终于无法医治了。 去年腊月二十一,接三妹电话,心惊胆颤地急匆匆回到家,看到坐在炕上浑身肿得像米面佛(弥勒佛)一样的父亲和满屋子人,不由得泪水再次夺眶而出。眼睛肿得快要睁不开的父亲,反倒比我平静,劝我说:“不要紧,伯不要紧,当下死不了,你们快去吃饭!” 自己都这样了,他还惦记儿孙们吃饭。家人给我述说父亲治疗的情况,针已经打不进去了,四肢找不到血管,扎进去的肌肉针,药液都顺皮流淌了。西药更是进口就吐,吐得翻肠倒肚。医生都说器管衰竭了,就像一颗老树一样,不但叶子凋落,股股叉叉枯死,根也腐朽了。 预感到自己离世之日将不会太远,腊月二十三晚,父亲让我坐到他跟前,颤颤抖抖地从贴身口袋掏出两样东西交给我。其中一串钥匙,长长短短、大大小小一共九把。他拨弄着给我说:“这个黄的、最大最长的、上面抹了红漆的是头门上钥匙;这个短一点的、上面抹绿漆的是二门子上的;这个白的、碎的是门上农具房房钥匙,镢头、锨、粪笼、镰、花子绳、锤子、斧头和凿子都在房房放着;你看,这个二不流就(不长不短)的是粮仓门上的;这个是厨房门上的,这两个是里面院子两个厢房子的。他一把一把指教给我。还有两把,一个是他用9号铁丝砸的掏耳朵挖挖,一个是他用钢锯条和铁皮自制的水果刀刀。 交代完钥匙,他又交给我一个塑料包包,包了一层又一层,打开了是一叠人民币,一共二千八百五十八元。说实话,我当时有点生气。记得去年他病重时,曾交给我一张一万元的存折。这些钱都是我平时给他,他节省下来的。他说:“我一个死老汉,除了吃药,平时又不弄啥,留着你们用。”结果,我到银行取钱时,由于记不得密码,银行按要求要存款人本人到场。没办法,我又二次用车把父亲拉到银行,在监控前拍了照,钱才取了出来。当时把人折腾地那个劲儿,我撕碎存折的想法都有。那以后,再给父亲钱时我就反复给他叮咛:“给你钱你就用,千万再不要舍不得花了!”结果,他还是节省了这二千多元。我说:“我姐和我妹,人家侍候了你一冬,你把钱给人家去么!”父亲翻了我一眼,嘴里唧唧咕咕,但不知说些什么。 为了尽最大可能地给父亲治疗,咨询了几位医生后,请来了一位镇医院的业务副院长,经过半天的检查,最后决定从父亲的肩膀上进行皮下注射利尿针,奇迹果然出现了,一天一夜后,父亲开始排尿,两天以后水肿开始消退,而且渐渐地能进食了。此后便一天比一天见好,全家人欢欢喜喜地过了一个团圆年。这时我就奢望着父亲再恢复到从前,能坐上轮椅、拄上拐杖到门前晒暖暖。 父亲耳聋,但眼睛却特别的光亮,看得远,看得清。那几天,我守在父亲跟前。见他过一会儿瞅一眼对面墙上的挂钟,我就问:“伯,你看现在几点了?” 他说:“七点三十五了。”果然是七点三十五。我再问:“一晚上长不长?”他说:“咋不长,一晚上三十八个小时,急忙等不到天亮!” 父亲时而明白,时而又犯老年人的痴呆糊涂。因为尿频,控制不了自己,夜里便经常尿湿内裤和褥子。我和爱人便买了纸尿裤,但他不习惯使用,他便拒绝。给他穿好了,他便挖抓着撕掉。我对父亲发脾气,父亲低眉看着我,没有吭气,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亏了理一样,但却忌恨了我,生我的气。隔天早晨起来,他对我说:“你把我的钥匙给我。要不,我死了变成鬼,回来连门都进不来了!”我从抽笹里取出钥匙交到他的手上。父亲默默地细数了一遍,在确认一把没有少后,小心翼翼地装回了他的贴身口袋。 父亲到了他活着的最后那些天,意识开始模糊,基本上任何饭食也咽不进喉咙了,但有两件事让许多人都不可思议。 一是特别特别地香酒。只要有人来,他就向人要酒喝,让人又急又笑。而且时不时伸长胳膊,在空中划着半圆,抬头仰脖子,嘴唇嗫嚅,做出喝酒的举动。家人便给他准备了几箱酒,每次只给他喝那么一点,他便唠叨不休。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病重的人,却到临终忘不了酒。要的次数多了,我担心他的病情,就让人想着法子拒绝,有次给酒里兑了点水,结果盅子一挨他嘴唇,便被他噗、噗地吐了。方法使尽,终是无法制止他的嗜好,只好由着他了,再要就让人哄他一小盅了。每次看着父亲失望的表情,我非常地恼恨,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在愚弄父亲,一方面又希望父亲少喝点酒能多活几年。 一辈子体谅别人的父亲,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平静地过了年,又平静地过了正月十五,到了正月十八,吃过早饭,父亲叫了一声我的小名便开始昏睡,这一睡任谁都叫不醒了。由于心脏病,活着只能窄棱(侧身)睡觉的父亲,这一回是仰面朝上,呼吸匀称,睡得很放松,睡得很舒坦,静静地睡了三天,直到正月二十晚二十一时整没了声息。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可怜的老父亲,年轻的时候,由于日子过得艰难,活着并没喝到多少酒,人生的最后两年,却欠酒欠得厉害,临死都没有喝够,埋藏时便给他的棺材中装了几瓶,让他独自静静地品尝。 还有一事是父亲临殁的那几天总是不停地念叨着:“回,咱回!”“咱回先,咱快回!”而且越到最后他越念叨得厉害。你感觉他像迷糊了,又觉得他明白着呢!盖在身上的被子被他一次次揭掉,他指着脚地翻来覆去地总是这两句话:“回,咱回!”,“咱回先,咱快回!” 我说:“伯,这就是咱屋里,你就在咱炕上坐着呢,还要回哪里去?” 父亲对我的回答闻若未闻,还是一个劲儿念叨着这两句话。没有办法,他的儿女弟侄们就做出让他回家的样子,一遍遍地把他从炕上抬下来,放到炕跟前的沙发上。哄他说:“你看,这不是回来了嘛!”可是遍数一多,他却发现了问题,就问:“这是在车上坐着吗?” 他的儿女弟侄们就七嘴八舌地回答:“是啊,这是车!” 他就问:“那车咋不走呢?” 大家意识到,他并没完全糊涂。就两个人把沙发搬动弹,轻轻地摇。 他说:“着嘛,就这样走,走快些!” 过一会儿,他用手在沙发扶手旁边摸,摸出了不对,就问:“这车咋没有轱碌呢?” 我说:“轱碌坏咧,来,咱重新换一辆坐!” 大家又齐动手,把他轻轻地抬回炕上,给他背后多垫几个枕头和被子。“你觉得这辆车咋向?” 他说:“好着呢!” 可是诡计总是很快就被他识破。他就又是那句:“回,咱回!” 没办法,我们就只好这样反反复复地把他老人家从炕上抬到沙发,再从沙发抬到炕上。 我一直在想,父亲到底要回哪里去? 心理学家们说,老年人想的都是年轻时的事,特别那些让自己刻骨铭心事。父亲莫不是又回到了他小时候带着五叔在山后开荒的年月——遭饥荒、挨冷冻、斗野狼…… 从前也曾听人说过,人在临终时,就要“四大分离”,就会有很多境界出现。所谓“四大分离”,据说是地大、水大、风大和火大。一个正常因老因病而死的 人,死亡之前,“四大”先起变化。 首先是地大发生障碍。人体的地大是骨节、筋骨。所以年纪大了的人,没有知觉了,筋骨、神经死了,身体像被重物压住,不能动了,那个压迫像两座山挟拢来一样的难受。病人恍恍惚惚感觉自己到了一个地方,很黑暗。父亲可能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他于是就要急着回家。 接着是水大分散,这时候病人的两个眼睛瞳孔放大,你虽然站在他面前,他看你距离好远,像一个影子一样;你跟他大声讲话,他听到像蚊子叫一样。他身上出冷汗,这是水大分散。水大分散的时候,病人意识分散,好像进入梦境,其痛苦比梦魇还难过。病人可能感觉自己掉到水里去了,听到水声哗啦啦的响,实际上是身体内部发生变化。 水大死亡之后,跟着来的是风大分散,病人气马上要没有了。这个时候,气上不来,说不出话了。气到了喉部,病人进入完全迷糊的境界里,感到风把自己吹得又冻又冷,最后,呃一声,气断了。 风大的死亡一步一步上来,同时连到火大的分散,病人体温跟着风大的分散一步步丧失,一步步变凉。喉咙不停地呃……呃……最后一口气不来了,整个身体也冰冷了。 那一天,当父亲的“四大”散尽,躺进棺材,全村人抬着他走向三十亩地(坟墓所在地)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一辈子和黄土打交道的人,殁了还离不开黄土。父亲要回去的地方就是这儿——就是这一片黄土地!难怪他病着的时候,多次给子女嘱咐,将来他殁了,把他埋到三十亩地。不要箍墓,就掘个墓坑,挖个窑窑,棺材能放进去就行了! 我披麻戴孝地跪在稀泥烂透的黄土路上,让自己的眼泪和雨水一起放纵地流淌。我嚎哭着告诉他:“伯喔——你不是不停地要回家吗?今日全村人都回来了,他们坐着飞机、乘着火车、开着汽车从北京、从上海、从深圳、从杭州、从江苏、从甘肃、从西安、从咸阳……从祖国的各地都赶回来了。回来给你送行来了!今天他们就要把你送回家了——送到你向往的喔片三十亩地里去了!你就静静地躺到喔达陪我妈去吧!你放心,你留给我的钱我不用,我要把它捐给咱村里!” 在一阵嘀嘀呜呜的唢呐声中,一阵儿女子孙嘶心裂肺地哭叫声中,父亲离开了他住了几十年的家——回他的老家——三十亩地里去了!
作者简介 董怀禄,笔名小河水;新浪博客和微博昵称:长安亦君;微信和QQ昵称:细水长流。中学高级教师(现已退休),十堰市首届十大名师,中国中学骨干教师。中国新文学学会、中华精短文学学会、作协十堰分会会员,原十堰市语言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乡土文学作家,精短小说签约作家,西部文学副主编。作品见诸多种报刊杂志和网站,多次荣获文学大奖。出版有个人专集《怀念与忧思》、《黄土魂》、《董怀禄短篇小说选》、《家在牛角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