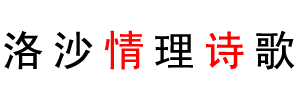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挠头的事,恼人 又是一个庚子年。本应是个快乐祥和的年,却被武汉的冲击波,给冲没了。 这个年的特点,便是全国人民自我“关禁闭”。不用想,时时刻刻都能清楚的记得,已“封闭”快三十天了。 当然,这些天里,除了考虑吃、喝、用度,还在为武汉着急,为家里在外“抗疫”的人担心。什么都急,什么都烦。不成想,没考虑到的事,也来凑热闹。这不,头发渐渐地长了,成了需要“挠”的问题,虽不担心,却恼人呢。 中国人过年的习俗,有一件事也很重要。那就是,男人必须在腊月里,最好是二十三以后,除夕之前,理发。当然,也有人可以不理发,而且,是不能理发的。原因吗,在这里就不说了,留给大家猜吧。 有句俗话说:“痴人顶重发”。真的,这句话在我的身上应验了。年轻时,满头黑发,不仅密,还粗,每根都直愣愣地挤在一起,像个刺猬。乡亲们说:这小子,实在哩。 长大后,进城,参加了工作。在男男女女交织的世界里混,没人教,便“自学成材”,知道了臭美。 呵呵,除了穿衣戴帽,最重要的,便是修理这一头“重发”。 也不知道是从那一天开始的,每个星期都要进一次理发店,似乎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起初,在工厂里上班,工作时间是要穿工作服的,还要戴工作帽。无论如何,头发不能乱。因此,戴帽子也是有讲究的,若戴得不正,不在那个特定的“水平线”上,头发一定会被弄得乱七八糟。交给理发店的三块钱,算是白交了。 从小,就喜欢“三七开”的发型。可小时候无条件,没办法实现这个梦想。有能力,进得起理发店了,在电吹风和发胶的作用下,想要个美观、理想的发型,似乎很容易。但是,要将发型保持好,保持得长久些,却不容易。根本,要看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比如这戴帽子,要先将头发拢好,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帽子的后沿从头前,按顺序向脑后滑动,滑到脑后跟了,停住。轻轻地,将帽子的边际,扣在耳朵跟稍上些的一条水平线上,再回手沿着帽边,分两侧向脑门前移动,将自头顶上分散下来的发稍压紧了,压顺了,才行。然后,将脑门上还有些散落在外面的头发,分捋到两边,能被帽子扣住的扣好,不能扣住的,任其漂洒着。既自然,也不会破坏了原来的形状。 不到三十岁的时候,胡子齐刷刷地长上来了。这胡子吧,还有些特别,络腮连鬓不说,跟头发一样,既粗壮,又浓密,就像是一副板刷子似的。 才开始,理发是不需要修面的。胡子长出来了,用手拔。手拔不了,用夹子夹住了拔。有时,还用“活血止痛膏”贴在胡子上,使劲地撕,以达到拔胡子的目的。 据说,用这样的方法,拔掉的胡子便不会再长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到是因为拔胡子,拔得血流满面。脸上,还长了很多疙瘩。有些疙瘩发炎,都长脓了。 当然,这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的理发员,几乎都会修面。通俗的说,就是会刮胡子,只不过水平高低不等而已。故乡的小城,是解放初新建立的,老街、新路四五条,大约有近十万的居民。 自古以来,理发是不老的职业。理发店,便是遍布大街小巷的营生。早先,理发员基本上都是男的,后来,女人也介入这个行当,还越来越多。其势头,几乎盖过了自称“大老爷们”的男士。而且,很多女人们的手艺,比男士好。加上女人的温柔、体贴、细心,以及女人特定的身份,似乎更适合这个职业。也因此,女人经营的理发生意,非常的火爆。 我需要的,既有很好的理发手艺,还要会修面,也就是刮胡子要“有一手”。 有段时间,我在不同的大街小巷里,选择不一样的理发店。其实,就是想试试每一位“大师”的手艺。电影院附近,有个L师傅开的店,一间屋子,一把椅子,一个人操作。L师傅也就是二十几岁的年纪吧,高高的个头,有些单薄,不算漂亮,也不丑,还不喜欢多说话,只会闷声干活。但是,手艺不错,洗头认真,洗得干净。尤其是刮胡子的技术,堪称一流,是我试过的几十个“大师”中,最好的。 她刮胡子,自始至终,不徐不疾,稳稳当当。刀在皮上走,手在脸上滑,热毛巾跟着拂过来。剃刀的一落一起,既轻,又重,还稳。轻,是下刀轻;重,是刮起时有力量;稳,是刀的力度、速度适中。一刀刮过去了,似一阵清风挠过,没有一丝一毫的灼痛感。 我理发,刮胡子是“重头戏”。面积大、粗状、浓密且不说。关键的是,不同的位置,还是不同的走向,不同的顺序。最最棘手的,是两腮处起旋了,像形成的龙卷风,紧紧地围绕着一个“带”,或是一个中心,逐次地展开。令很多“大师”的刀,居然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没弄明白,L师傅是怎么处理的,只是觉着,她的刀到了此处,力度更大些、强些,是那种毫不犹豫的,一刀就“劈了”过去的。接着,下一刀又来了,也就这么三刀、两刀的,解决了。 每次,L师傅在给我刮胡子的时候,我都是静静地躺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闭上眼睛,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调整好气息,以最轻松的状态,配合着她的工作。她的刀“一落一起”,我便记为一刀。从第一刀起,默默的数着,待到她最后的一个“落起”完成了。她在我的脸上,约刮了五百刀左右。我起身整理衣服时,跟她说:“你可知道,刮了多少刀吗?” 她嫣然一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当听到我报出的这个数字时,一愣,然后,吐了吐舌头,似不信,又不敢不信。说:“真的,这么多!” 这是我多少次理发,与她的唯一一次交流。 四十岁左右的时候,感觉头发软了许多,也少了许多。而且,还有些泛黄,没有了曾经的“乌蓬蓬,亮晶晶”的质感了。有人说,这是经常吹头,被电吹风灼伤了。从此,我便不再吹头发了。但是,每个星期理一次发,刮一次胡子,还在继续的坚持着。 五十多岁时,大街上的理发店,几乎是在一夜间,变了。门面讲究了,宽敞了。“理发店”的字样,大都换成了“美容美发”。还有的,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叫“会所”、“会馆”了。似乎跟理发不搭界,又确确实实就是理发店。理发师,清一色的,都是俊男、美女。店内的装潢也非常的时髦,既有档次,又很温馨。就如同小城一样,路宽了,直了;楼多了,也高了。总之,变得漂亮了,有品位了。 理发的最大变化,是女人比男人多。洗头不再坐着,改为躺着了。男人理发,只理不修。就是只剪发、做造型,不刮胡子。几乎所有的“大师”们,都不会刮胡子。还有,就是涨价了。尤其是女人美发,一次没有百元,恐怕出不了“会所”的门。 我们这些“半截老头”,也得跟着改革。我呢,不吹发,不做造型可以。一个星期不理一次发,是不可以的。我容不得头发长了,刺耳朵,蹭衣领。刮胡子的任务,只能留给自己了。 起初,使用的剃胡子工具,叫剃须刀,也叫保险刀。使用时,先在胡子上涂上肥皂沫,带着肥皂沫刮。刮时,要小心,慢慢来,弄不好会刮破脸皮,弄得血染白沫,浸透毛巾,那个疼哟。 好在,我们已进入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商家尽心尽意地为我们“胡子一族”着想。各种电动剃须刀如雨后春笋,急速地走向市场。自然而然,男人们,尤其是“胡子一族”,都会拥有不俗的电动剃须刀。 “我的脸,我作主”了。二三十年来,我用过多少把电动剃须刀?可能是两位数,甚至是三位数了。 眼下,我已是年过花甲之人。这满头满脸,也在向夕阳看齐。最明显的,这头发又少了许多,软了许多。特别是头顶部位的一大块,差不多全“露天”了。而四周呢,依旧茂密葱茏,只是变成了花白的颜色而已。还怪呢,脸上、腮上、唇上、下巴处的胡子,除了变成白色,其长势还是朝气蓬勃的,没有片刻的停滞。 去年的腊月中旬,我便理了一次发。拟在除夕之前,再理一次发。这,不仅是风俗习惯的需要,也是我不喜欢养长发的本意。不成想,春节的杂事太多,给耽搁了,除夕前没理成。心想,这也不打紧,正月里,初四就有人开门营业。最多,到了初八,美容美发的师傅们就基本复工了。迟几天,也不是什么大事。 天下事,就是这么难以预料。谁能想到,庚子年,这么不平凡,这么恼人! 人都待在家人,是这个年的特征。不得已,要出门,得戴上口罩,和遇见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理发也好,美容、美发也罢,都只能关门歇业。最普通的事,变成了最不可求的事了。 正月已经结束了。人们差不多有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没理发了。可是,“新型冠状病毒”还在蔓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根除。听说,近两天理发店可以开门了。即便,它营业了,人们敢去吗? 我的头发,早已到了该理的时间段了。当然,头几天里,只是感觉头发长了,还没有其它的影响。初十左右,先是后脑勺下的脖梗处,发际线的结合部,那一簇簇茸茸的细毛,不随我的意愿,不听任何势力的阻挠,径自长上来了。虽是小心翼翼的,卷曲着,交织着。却大胆地冒过衣领,毫无顾忌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不敢对镜理装,害怕看到它们。稍不注意,在镜中看着了,浑身便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弄得我不敢进洗手间,为的是躲避眼睛。但是,手却不行,忍不住了,便要摸上一把。摸着了,就想捏住,就想拔了它。说你不信,手能摸得着,也能捏得住,却拨不掉。那个急哟! 我不喜欢两边的鬓发扎耳朵,更不能容忍软软的头发搭在耳朵上。那样,我会赶夜去理发店。剪去了耳朵上边的头发,会觉得头轻目爽,走路都会有脚底生风的感觉。 现在呢?耳朵上的头发,不仅仅是搭在上面,几乎是披在上面了,那个难受哟!弄得我,日日夜夜的双手挠头,似乎要将满头的头发挠完了,挠光了,才会舒服。 没办法,只能洗头、洗澡,几乎是一天洗一澡。 问题又来了。两三天的洗下来,先是腿上、胳膊上痒痒。接着,后背处也痒痒。某一处痒痒,伸手挠一下。坯了,越挠越痒,是那种无法制止的,钻心的痒。挠了一处,本来不痒的别处,也痒了。这里挠挠,那里挠挠,嘿,满身都痒,两只手根本挠不过来。这个难受哟,跳楼的心都有了。 网上一搜,知道了。上年岁的人,身上油脂少了,洗澡不能太勤。皮肤缺油,便痒。你说,这是什么事! 胡子呢?不屈不挠地长着,剃须刀天天都充满了电。 我没有L师傅的手艺,不知道怎么用刀。当然,剃须刀的刃是藏在里面的,不会伤了皮肤,就“放马”过去吧! 每天,或是早上,或是什么时候有空了,拿起剃须刀,不需要镜子,不需要水,更不需要肥皂沫。一个人,躲在一个不影响他人的角落里,耐心地上下揉搓,安静地聆听着磁磁的声音。 我的脸,我的腮,我的下巴…… 忽然,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位老领导,也是一位“大胡子”。在他五十岁左右的时候,满头便不见一根头发了,胡子却长得满脸、满腮密密麻麻的,几乎看不见皮肤。这位领导,开朗、风趣、幽默,无事时,喜欢和同僚们开玩笑。说到头发和胡子,他的经典段子是:“你不让我露头,我便不让你露脸。” 他把头发、胡子拟人了。说头发、胡子,对人们理发、刮胡子的行为,非常地不满。不是动不动就拿刀子剃,刀子刮嘛!哼哼,你剃,你刮吧,我一个夜晚就“春风吹又生”了。想不让我露头,我还不让你露脸哩。看看,谁怕谁呀! 他说这话时,不笑,也不大声,慢条斯理的,就像是在回答古往今来,人们总是欲说还休的一个神话。 但凡听过他说这段子的人,都会在一个愣后,笑得前仰后合。佩服他说的精辟、到位。 老领导已作古好几年了。他的段子,记忆犹新。这个段子含蓄、好笑,是因为他说明白了一个道理。世间事,都是有规则的,都要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序间进行,才能有好的结果。 而庚子年的事呢?看起来是突发的,是武汉闯的祸。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应该是很多事情做得过头了,过火了。比如,大吃、特吃野生动物。动物们被伤害了,地球的生物链被破坏了,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你不让我露头,我便不让你露脸。 我的脸,露不露的,问题不大,待在家里不出去好了。我的头呢?头发长了,长了很多很多。真的是露了,露得麻烦,露得揪心,露得无所适从。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挠了。 挠头事哟,恼人! 2020年2月25日写于合肥巢湖之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