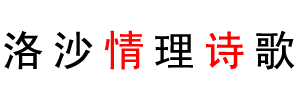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握手班禅大师
作者 梁旺俊,男,汉族,陕西合阳县人,早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先后于部队和地方歌舞团从事器乐演奏多年。1990年代开始从事地方志编纂和藏族地方历史研究,主编出版的《碌曲县志》,结束了碌曲县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关藏族历史的论文有《藏族的部落制度》和《藏族部落的政治与经济》,2009年退休,现居西安,长于纪实文学写作。
1982年秋,回到内地没有几天,忽然接到单位发来的一份加急电报,电文是:"有重要演出任务,速回勿误"。回到单位方知,藏传佛教领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要来甘南视察。 消息像是长上了翅膀,很快就传遍了村村寨寨。当地政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和歌舞团的节目排练也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最兴奋的还是寺院的活佛僧侣和农牧民群众,人们纷纷忙着置办新衣,大街小巷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1975年秋我刚到甘南,革命大批斗活动还在持续,不过对"牛鬼蛇神"和"阶级敌人"的批斗,不再像运动初期那样,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挂上大木牌戴上高帽子游街了,斗争的手段文雅了许多,虽然还是恶语相向,蛮横不讲道理,毕竟有些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之风了。 革命大批判在民族地区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在内蒙古受到批判的有乌兰夫,藏族地方,除了刘少奇、林彪和死了2400多年的孔子外,还有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和早就没有人身自由的十世班禅。在歌舞团政治学习室的一个角落,堆放着一捆资料,上面布满了灰尘,我抽出一本以探究竟,资料封面是醒目的仿宋体《达赖班禅反动言论摘录》,里面的内容用的是藏汉两种文字,左边是藏文,右边是汉字。这种文字形式的批判资料,在那儿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即使是歌舞团的藏族演员,也没有人认识藏文,他们的汉文水平也不大好。 差不多两个星期在政治学习时就要开展一次革命大批判,口号是大批促大干。那时我还是个糊涂虫,没有政治辨别能力,文件和报纸上说什么就信什么,只是对没完没了的集体学习和革命大批判感到厌烦。报纸上说刘少奇要复辟资本主义,让全国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头遍苦刚吃完,再接着吃二遍苦,肯定是不行的。 写批判稿是政治任务,写好的稿子不仅要在批判会上念,念的时候还要有很生气的样子,表示极大的阶级义愤,然后还要张贴在墙上的革命大批判专栏里,供上级检查来的领导看。批判会和批斗会不同,批斗会的对相是活着的当地的牛鬼蛇神,打的是活靶子。批判会批判的大多是早已进了棺材的,放的是地对空导弹。写批判稿也都是抄抄报纸,当时流行的是"小报抄大报,大报看梁效"。看到《人民日报》常有梁效的文章,我很兴奋,还自豪过很久,我以为我们姓梁的也出了个人物,可以和姚文元一见高低,后来才知到,梁效不是人,而是"四人邦"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学校组织的御用写作班子。 革命大批判闹过不少笑话,一个演员看别人写批判稿抄报纸,也找来一张报纸一字一句抄了起来,该他发言时他念到:据路透社报到,基辛格……笑的大家前仰后合,原来他抄的是《参考消息》。一次单位领导问一个藏族演员孔子是什么人,他摸着脑袋想了想回答:听说是毛主席的秘书,和林彪搞到了一起,毛主席很生气,所以就要在全国批判他。看见大家都在笑,他反问道:怎么说的不对吗?反正是个大官,走资派。那时社会上的人对演员的评价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实际情况是,就文化素质而言,确实有些不大好,尤其是舞蹈队的,这些事在现在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革命大批判在藏族地区都会涉及到班禅,说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封建农奴制,在我的记忆里,达赖喇嘛和班禅截然不同,对于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两个人的态度大相径庭。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3月17日,达赖及其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逃往印度。与达赖不同的是,班禅则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和政府的一边,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和民族团结,人们称他是伟大的爱国者。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 在极左思潮时期,真要实事求是起来,要么惹来杀身之祸,要么倒不完的霉,就像莫言说的,那时说实话是要受到惩罚的。 和彭老总一样, 班禅副委员长的厄运也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1961年国庆节后,班禅副委员长到云南、四川、青海考察调研。1962年夏天,他就内地藏区的极左倾向,从而联想到西藏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问题,给国务院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及其他地区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从报告的标题来看,他的汉语程度和他要表达的内容,有不小差距。报告共7万字,对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不少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建议他将报告的内容,以口头形式进行汇报,以免惹出麻烦,性格直率的十世班禅,对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残忍性缺乏认识,坚持以书面报告上报中央。 一年后,"七万言"报告被说成了"反动纲领",与彭老总的"八万言书"相提并论,说他两个是一个在党内一个在党外,里应外合向党猖狂进攻,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问题的性质会有多么严重呢?伟大领袖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1964年9月,班禅开始受到严厉的批判,被扣上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3顶帽子,他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被撤销。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十世班禅也在劫难逃。 1966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中央民族学院的造反派,不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翻墙闯入班禅住处,将他五花大绑,押到中央民族学院。造反派私设公堂,对他拳打脚踢,吐口水,揪耳朵,边打边骂,恶言相向,之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和游街示众,大而重的木牌挂在胸前,铁丝在脖子上勒下了深深的疤痕,穷凶极恶的北京红卫兵还成立了批判班禅指挥部和联络站。 为了保护班禅,北京卫戍区和中央统战部根据周总理指示,经过多次交涉,与红卫兵达成了两项协议:1、只能联合召开批斗会,不能轮流批判;2、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捆绑不能"坐飞机",只能联合批斗1次,结束后交回卫戍区,押送工作由卫戍区负责。 1968年夏,他被送进了秦城监狱。那时的秦城监狱,成了林彪"四人邦"迫害大批老干部和爱国人士的地方,一间八九平米的监舍,一床一桌一椅,窗子上一个漏斗状的小孔,密切注视着年仅28岁的班禅的一举一动,直到1977年10月,他才获得了自由。 历史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曾经对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不满12岁的班禅,派出使者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立刻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表示衷心拥护中央人民政府。 1952年春,在返回西藏途经那曲时,拉萨发生了反对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成立"伪人民会议"事件,一些骚乱分子围攻中央代表驻地,他怀着极大的义愤致电达赖喇麻,谴责这种破坏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恶劣行径。 解放军进藏之初,西藏上层顽固分子处处刁难,有的说打不过汉人,在西藏的地盘上,总可以饿死他们。班禅得知后,向中央代表捐献粮食50万斤,还让自己的寺院给日喀则的部队送去米面牛羊。 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与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一同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重新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 1988年4月,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班禅副委员长在回顾自己的历史时,表明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感激之情,他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每逢1月8日,他都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周总理献上花圈和哈达,寄托自己的哀思与怀念。 因七万言书获罪使班禅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深陷囹圄的日子里,他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觉得寂寞而又孤独无助,他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渴望能够得到关怀,尤其是在秦城监狱,当他看到別的人有亲人探望时,回归社会的欲望十分强烈。 磨难使他悟出了人生的真谛,作为僧侶,他清心寡欲,苦心修炼数十载,过着青灯古佛的日子,从未有过踏入红尘的意念。出狱后一次他对朋友说:我年轻时为祖国效力,后来被安上子虚乌有的罪名,60年代被囚禁在监狱里,每日里诵读佛经,以信念为我被限制的自由和受伤的心灵洗涤,被折磨了10多年,更让我懂得了珍惜二字,希望能有一位红颜知己。 一次,他在火车站与一位姑娘相遇,心生爱慕,然后就去了解她的情况,得知这位姑娘叫李洁,是开国上将董其武的外孙女。李洁不仅漂亮,还是第四军医大学的高材生,他开始有意接近将军的副官,委托副官为自己物色个妻子,副官请李洁女士帮忙,李洁说是要见见那个要找对相的人,了解他要找个什么样的对相。没想到李洁和班禅一见钟情,就这样,20岁的李洁嫁给了40岁的班禅,那时他头上的三顶帽子还不曾卸掉,政治前景并不明朗。1979年他们结了婚,后生有一个女儿,从此以后,依照藏传佛教教规,班禅不再身着袈裟,而是只穿华贵藏袍。 1982年9月中旬,班禅副委员长来到甘南视察,随行的有他的父母及中央和甘肃省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新闻记者数十人,甘南州的党政领导及宗教界上层人士前往土门关迎接。 土门关位于临夏与甘南的交界处,曾经是茶马古道的重要关口,在明代著名的24关中,土门关为其中之一,走进土门关就是步入甘南藏区。土门关以北是黄土高原,是回族居住的农业区域,以南属于青藏高原,是藏族牧业区,不同的地貌形成了色彩对比鲜明的生态奇观。 从土门关到自治州首府120多公里,沿途站满了附近村庄和寺院欢迎的群众和僧侣。在土门关,前来迎接的当地党政军领导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向副委员长及其一行敬献了哈达。 国庆节前夕,班禅副委员长一行来到我工作的那个地方视察。那天秋高气爽,像是盛大的节日,街道上挤满了穿着新衣面带笑容的各族群众,10时许,人们终于等来了渴望已久的时刻。 高大的身躯,慈祥的笑容,那一刻,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在离欢迎人群不远的地方,他下了车,和身旁的人用藏语嘀咕了几句,然后款步向人群走来,一张张笑脸向着大师,他走走停停,不时向夹道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歌舞团的演员们跟在后面敲锣打鼓,在副委员长身后有两位老人,一位藏族演员告诉我,那是大师的父母。 晚上是歌舞团的演出,演员们既兴奋又紧张,那时独唱节目乐队需要上台伴奏,我的位置在舞台的边沿,与副委员长也就两米多,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那张慈祥的脸上。板胡独奏时,往常的演出处于习惯状态,比较自如,那一天不同,总怕出错,走上舞台的那一刻,神情似乎有点恍惚,在我努力想使自己镇定下来的瞬间,我的目光又一次落在了他的脸上,他微笑着看着我,我的紧张感立刻消失了。演出结束后,班禅大师和一行领导走上舞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班禅副委员长身材魁梧,他的个头在1米8以上,他说自己是个胖活佛,与群众交谈时,总是面带笑容,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与他握手时,他微笑着看着我,那一刻我的心里完全没有见到大首长的敬畏感和陌生感,我觉得他像是我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又像是令我敬仰的那些与人为善的长者。 一天傍晚,广播里传来了他的声音,那时他正在对当地的领导干部讲话,他的声音温和而富有磁性,我站在一处有大喇叭的地方倾听,直到他的报告完毕。他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落实民族政策,特别强调要搞好民族团结。一个时期,民族排外情绪有所抬头,汉族干部人心惶惶,尤其是科技人才流失严重,他的讲话对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稳定十分重要。 多数时间,他都在深入基层,一方面了解实际情况,一方面从事佛教活动,甘南是个全民信教的地方,每到一处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摸顶赐福,满足信教群众的需求。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不仅当地人,不少毗邻地方的人也远道而来,排队摸顶的人,主要是藏族干部和群众,有时还有些汉族干部和群众,遇到他们,副委员长也笑了起来,摸顶赐福也是个辛苦的事,有时他的胳膊又疼又肿。 大约40多天,班禅副委员长走完了甘南的大部分乡镇,4.6万平方公里的草原,地域辽阔,村庄分散,道路崎岖,不少地方海拔在3千到4千米,高寒缺氧,只要能去的地方他都前往。自自治州建政以来,即使是当地的党政机关领导,还没有一位能像班禅副委员长那样,用几十天时间,走遍了甘南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