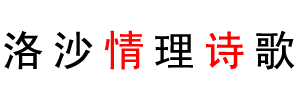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春节到,年味浓。春节对于我们中国人,是传统意义上的年。 春节年年过,随着自己的年龄与岁增长,每年过年的感受略有不同。我觉得2020年像是自然界对人类动了惩罚烈怒,或者像脾气乖戾的孩子。蝗灾肆虐,气候异常,森林火灾,新冠嚣张,风云变幻……春冬时间长,夏秋蜻蜓点水,一闪而过。我想这绝非我一人的感受,是绝大多数人的内心实感。 去年过年,居家隔离,历历在目。 当时武汉新冠疫情牵动全国,经当地医护人员和全国多地的医疗小分队驰援,历经76天的艰难奋战,国内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夏、秋季国内疫情防控总体很好。但因全球疫情蔓延和新冠病毒的变异,防控形势严峻。因境外输入,致使我国数个地方有疫情星点反扑现象。给过年团聚带来影响。但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我们应自觉遵守国家及地方上的防疫政策,就地过年,不给国家疫情防控工作添乱。今年过年,自觉居家,安全稳妥。 小时候,我感觉年味特浓。那个时候虽经济落后,物质较为匮乏,但许多过年的吃食多数自制,所以在我印象中,过年仪式感强。 进入腊月,就慢慢进入了筹备年的渐进模式。家家户户都开始忙活起来。挑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清晨,在母亲带动下,家人早早将窑洞内的盆盆罐罐,能够搬动的所有家什,全部搬到院子。然后家人齐动手,进行大扫除。窑洞内角角落落,都要打扫干净。紧接着用新报纸将土炕墙裙糊一圈。窑洞里的东西在太阳下晾晒多半天,下午太阳西斜,再一件件将东西搬进窑洞内,一一归位。 紧接着是捡麦、磨面。(捡麦是人工挑去麦粒内的小杂质,如土粒,料角石。磨面,要去村里的磨坊磨面,因过年家家待客需白面,所以经常排队。)赶集买猪肉,煮肉,杀家养的土鸡,换豆腐,蒸馍,打凉粉,炸焦叶(油炸的菱形面片,大小为长对角线约10厘米。)炸肉丸子,蒸肉碗。母亲要提前给我们姊妹几个张罗着剪裁并用缝纫机缝制新衣服。姐姐放寒假,她懂事地主动分担起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用一副简单的竹毛衣针,给我们姊妹四个每人织一双毛线袜。 那飘着煮猪肉的香气和油炸焦叶的年味,早在我幼小的心中充满渴盼。因为年到,就可以吃到白馍了。当然这是我五岁前的记忆。往后,家中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不再缺吃的。 过年蒸白馍的时候,顺便要捏数盏小面灯,蒸熟。面灯形似圆台状,上顶面捏成凹状,形如小碗。除夕之夜,在面灯内倒些菜籽油,剪一根粗棉线,一端浸在油里,另一端搭在灯沿,就是一盏简易的油灯。在院心、照壁中央预留的土地爷的神龛内,大门口东墙预留的灯窑内,以及院门口两侧的门墩石上,逐一摆放面灯,点灯迎福,以恭敬姿态迎接新年到来。后来过年面灯与时俱进,改用红蜡烛代替。 父亲过年休探亲假,常常要到腊月二十九或者三十才回来。所以父亲到家,母亲基本上将绝大多数的过年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记得父亲过年回来,每年都会乐此不疲地做他拿手的几道菜:干煸带鱼、爆炒肉丝,拔丝香蕉,油炸藕合。此外,父亲每年必做南糖花生,将制作好的南糖花生趁热转入不锈钢饭盒,定型后,再从饭盒翻扣出,切成薄片,给我们姊妹几个当零食。 腊月三十,母亲通常忙碌熬夜到子时以后,父亲将初一早晨包饺子所需的肉馅剁好。临睡前,母亲要给我们姊妹几个逐一把新衣服套在棉衣、棉裤上面。乡俗习惯称院门正对着的窑洞为屋,与院门偏斜的窑洞为窑。屋是主位,窑居次位。所以家人住在屋内,分睡炕和床。屋内生炉子,暖和,东窑内没有生火,所以过年的东西都在东窑存放。气温低,馍和熟食不易变质。冬天不生火的窑洞内就像是巨型冷藏室。 大年初一,大人小孩都穿上新衣服。虽做不到里外都新,但至少外罩是新的。有时是用白布自染色而成的或红或蓝或黑的布料,经母亲巧手剪裁缝制,穿起来照样兴奋异常。后来条件改善,过年新衣不再自制,改买成衣。 初一早晨,母亲早起和面,准备包饺子。父亲在灶房拉风箱烧水,姐姐擀饺子皮,母亲包饺子,我剥蒜,捣蒜泥。每年过年,都会将两枚新硬币,混包进饺子中。饺子下锅时,弟弟就高兴地到院子里放一串鞭炮。家家户户都在抢先响炮,早响,意味着早吃饺子早有福。 饺子出锅了,家人围桌而坐,吃团圆饭。当然配饺子还有六盘美味的菜肴。家人都在看谁能吃出硬币饺,那么吃出硬币者这一年都有福气。吃完饭,母亲会带着弟弟或者我去邻里家中给长辈拜年。 小娃过年穿上新衣服,很想显摆,所以呼朋引伴在槐院(老家称巷道为槐院)痛快玩。寒假作业已早早写完,所以没有作业压力。过年就过个欢乐放松的年。晚上,小伙伴又聚到一块,放熄熄眨眼,摔炸弹。玩熄熄眨眼的时候,通常会很卖力地抡胳膊划圆,形成一个闪闪的亮圈,小伙伴们互相比拼,看谁划出的亮圈大。 最热闹的要数正月十四、十五,邻村赵庄,几乎年年耍社火,踩高跷,扭秧歌,很是热闹。我与小伙伴们跟着姐姐与她们的同伴们,一溜一串,浩浩荡荡,一二十人结伴同行,去赵庄看社火。到赵庄看耍社火的人很多,方圆十几里的人聚拢来,人山人海,就像赶大集。在赵庄村的村头空场院或者进村主路两边,自然成为一街两行的临时集市。有卖油糕、水煎包、小笼包的,也有卖糖人、甘蔗、糜子糖、风筝的,也有卖簸箕、高粱糜笤帚、小农具的,当然最多的是兜售各式各样的花灯笼,以纸灯笼居多,也有兜售小娃燃放的各式花炮、礼花的。到赵庄肯定是先看耍社火,看尽兴了,返回的时候顺路到临时集市上买几盏灯笼和几把小红烛,或者买适量的礼花、礼炮之类,晚上集中燃放。 记得有一年去赵庄看耍社火,临时集上有一家摊点卖玻璃灯,正方形,小巧玲珑。方形玻璃顶盖中间割成圆孔,圆孔上方是一块用红油漆刷的小铁皮,呈圆圆的小荷叶形,灯笼底托是一块正方形的厚铁片,四边焊接的是边宽约6毫米的角铁皮,四周每片玻璃中心位置彩绘着花卉图案,看着非常漂亮。用一根二尺长筷子粗细的小铁棍挑着荷叶顶罩上的小铁环。做工精致,招人喜爱。我上前询价,有点贵。姐姐见我渴望的眼神,给我把玻璃灯买下来。回家路上,我拿着玻璃灯,一路走得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摔上一跤,将玻璃灯打碎。那个玻璃灯我玩了好几年。平时就用报纸裹着,放在高处不易够着的石瓮盖上,过年的时候再拿出来玩。那个时候,我们村过年不闹社火,而是唱大戏。村上的戏班子早在冬闲的时候,在大队部的院子已经排练好,单等正月初十左右在大队礼堂隆重上演。 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看古装戏里的小姐、丫鬟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出场。小娃看戏图热闹,至于看懂看不懂不是关键,能看个大概就行。再说看戏的时候,周围观众议论这出戏的剧情,对内容也有大致了解,绝不是看天书的状态。起码那个时候我知道黑脸的包公,红脸的关公,白脸的奸臣。小时候关于过年的记忆,是那样温馨,热闹,年味浓浓。 而今过年,人人捧着手机,发红包,抢红包。当然手机也有它的好处,在疫情防控特殊期间,无需东奔西走,我们用手机即可隔空视频,文明拜年,低碳环保,温馨健康。所以,虽然特殊时期我们不能到处奔走拜年,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居家过一个别样温馨、祥和的年。 年就像一个表盘,十二个月是它的刻度,转一圈,刚好一整年。过年对孩子们来说,是满满的期盼,又长大了一岁,又懂事许多,可以收到很多压岁钱。对大人来说,过年更多的是忙碌,是责任,是给亲人忙着准备过年期间丰盛的菜肴、礼品,给亲朋的孩子们准备分发红包。 过年对于成年人来说,是渐渐走向生命成熟的季节。不论是孩子蹿高懂事,还是成年人生命树年轮又加增一圈,都值得我们守岁、接福。 小时候,过年感觉是畅饱口福,幸福快乐,因为有父母筹划准备。而今,过年是成年人接过接力棒,是主力军,为人父,为人母,是义务,是担当。心境不同,自然过年感受不同。 世事板荡,防疫形势依然压力山大。但无论怎样,心向阳光,豪情满怀地跨进牛年的门槛,祈福,砥砺前行。开门迎春,笑脸拥抱这个美好世界。 闭目祷告,祈求安康;珍惜生活,迎年接福!
王文琴,女,作品散见于《现代作家文学》、《西部文学网》、《当代文艺》、《现代物业》等。韩城作协会员。系《现代作家文学》签约作家。用文字记录生活。已发表散文、诗歌、短篇小说、专业类文章过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