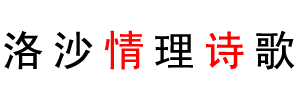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老 杜 文/王维宝
那是个如火如荼的年代。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设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全国人民从上至下积极响应。 秋收近尾时节,我有幸进了公社农田基本建设规划组。规划组工作就是把全公社的村庄、农田、道路、河流、林木等实际分布情况测量出来,然后做出新规划,再动员全公社人民施工,形成农林水一体化的高产“方田”。 规划组的正式成员有两人,杜光奇(音)和李继配(音),他俩都是业务型干部,在规划组里做技术员,杜光奇负责内业,李继配负责外业。 按公社的要求,农田基本建设三秋完闭后立刻开工,规划组的任务分为外业和内业,“亚历山大”。外业有李继配负责,是去田野打导线搞测量;内业有杜光奇负责,是在获得外业数据的基础上制定新规划,算出工程量,拿出施工方案,再把施工方案移交给管区具体施工。 外业分两步操作,先打导线再水平测量。于是我们这群小青年又分成导线组和测量组。为了赶进度,两组几乎同时下手,李继配一个人顾不过来了,于是又请来了懂测量的刘光明领着测量组。 杜光奇当年四十来岁吧,高个儿,长脸盘,络腮胡,浓眉大眼,书生相貌。说话温尔文雅,学者风范,与他相处时间长了,各工地来领材料的管区施工员呼他“杜水利”,我们几位规划组的小伙子天天都能见到他,时间长了便随着李继配叫他“老杜”。 老杜业务精湛,更是敬业,每天外业送来的原始材料都仔仔细细的审查,核实数据的准确性和完备性。当第二天外业人员出发后,他又埋头处理数据了。 有一天早晨,我们跑外业的按惯例来到规划组集合,准备出发。老杜突然一脸严肃:“昨天的水平数据闭合误差二十一厘米,太大了,今天重新测量!” 我就在测量组,负责记录观测值,搞这玩意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有些名词是才听说,在野外每次都是刘光明观测好了读出来,我再记录在本子上,至于数据的实际意义一知半解,刚才老杜口里的“闭合误差”乃是初闻咋见。 “什么?重测一遍,徐书记要求我们月内拿出中心地带的施工方案,你傻了!”刘光明急了。 “误差太大,不能通过!”老杜态度很坚决。 “你知道昨天测的是那条线路?下沟爬涯容易吗?到期完不成任务你负责?”刘光明一边诉苦一边责备他,我们几个跟随刘光明屁股测量的小喽啰也帮腔。老杜一下子火了:“好吧,我马上给徐书记打电话,让他负责!”刘光明一听害怕了“得了吧,不就是再重跑一遍吗,弟兄们走哇!”我们三个“小猴”在“猴王”带领下出发了。 这天刘光明特别激动,又加上我们对老杜的好奇,有问必答,这才多少知道了老杜的一些事儿。 原来老杜是个中日混血儿,母亲是随从日本鬼子来中国的,日本投降后留在了中国,嫁给了一个中国穷工人。老杜是老两口唯一的孩子,大学毕业生,学的水利专业(学校名称不知道),毕业后本来分在章丘县水利局,那年辛寨公社在全县第一个提出了规划“方田”的愿景,去县水利局要技术人员。局里非常支持,便派老杜、李继配一同前往辛寨公社的农林水办公室。 真糟糕,第二天的误差依然不过关,两人这才冷静下来,开始怀疑水准仪了,因为前段时间跑的都是单线,没有闭合测量当然感觉不出来。两天的闭合测量都有误差就值得思考了。按照那时的技术标准要求,允许区间只要不超过正负十厘米是可以过关的。请示徐书记后,决定有老杜领着我和另一个小青年去济南某维修点校正水准仪。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四十多年济南的不断发展和变迁,老杜家的详细地点没印记了,只是记得离杆石桥不远。去济南那几天正下连阴雨,我们俩没来几次济南,更别说什么杆石桥,迷向了,只能跟着老杜的屁股后面形影不离,把仪器放在修理部“住院”后又去老杜家里。 老杜家住的是他夫人所在单位宿舍。记得这所宿舍是多排平房,每户都是单间。估摸着老杜家的面积二十多个平方,内有两张单人床,再摆上一张办公桌和椅子,两个旧皮箱子,剩余的空间不多了。进门时一个老妪迎面施礼,本来就是锅腰子,在施礼时头更低了,几乎着地,口里还念念有词,听不懂。这种礼节我是第一次看到,不知如何才是。老杜告诉我们这是他妈,嘴角在微微颤抖。联想刘光明给我们说过的老杜身世,明白了几许。 近午时分,杜夫人来了,手里还牵着女儿,也就四五岁吧。杜夫人个子不高,身穿褪色的工作服,地道的济南人,说话“么么”的,简直把我俩看成是公社里派来的正式干部了,几句客套话后就开始诉苦。这时杜妈坐在靠里的单身床上,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同一个动作:身上那个包袱解了又系,系了又解……,杜夫人忽然冒火了:“你不就这几个包袱吗,值几个破钱,没人要你的!” 我俩几乎同时对望,想起动身前徐书记曾经叮嘱过:“不要在老杜家里吃饭,这是纪律”赶快告辞。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从水准仪校正以后,我们跑外业测来的数据准确了,每天都是一票通过,一周下来老杜的办公案上罗满了外业手册,叫苦不迭。有一天早晨徐书记来到规划组:“你们外业进度没问题了,内业老杜一人忙不过来,小王转内业吧。” 翌日,办公室里只有老杜和我,“内业”的风声虽然吹在我的耳边不是一半天了,但实质性的工作当属第一次。我屁股未坐定,老杜就拿来一份前几天积攒下来的线路高程测量手册,教我怎么利用永久性高程已知点为基准,依据记录册中各个桩号的前视、后视、转点观测数据,推算出各个观测点的绝对(或相对)高程,计算工具是算盘。老杜先给我演示了几个数据的算法,又眼睁睁的看着我打了几个数据,笑了:“小王的算盘有基础,很好,自己算吧。”转身忙他的派工单了,这份派工单很急,下午各个管区的施工员就来取。 经不住老杜的夸奖,我来劲了,一不留神就完成了一条线路的计算任务,老杜随便抽查了部分数据,全对!更高兴了“小王,我这次要对人了,以后你跟我学,不跑外业了,我会告诉徐书记的!”其实,老杜的算盘比我打的更好,刚才我曾偷偷地看过,算盘珠儿被他那纤巧的手指拨弄的如同行云流水,连绵不断,霹雳啪啦,响声连片,旁侧近赏简直是一种享受。 内业的工作量远远不止计算线路的高程,还要在此基础上绘制高程折线图,按照一级路、二级路、三级路的坡度,结合实际高程,在一定水准要求下设计路面和水渠,绘出每一段的或纵或横断面图、施工图和挖填土方量,给出土方调运方案,最后刻印成若干手册,及时分发到各个管区的分管领导和施工员手里。这些内业活儿,除了遇上天气不能去外业时他们搭把手之外,几乎都是老杜带领着我完成的,一干就是整个冬天。 在这个冬天里,工作室里的老杜和我偶尔也休息一会儿,简单聊几句,他不吸烟不沾酒,只喝茶。每次冲上开水那阵儿,伴随着茶杯口上方那簇簇缭绕的白雾,总有一股淡淡的茉莉香味向我飘来。 在那些日子里,老杜总是毫无保留,不厌其烦的赐教与我,使我在中学里学到的所有语文、数学、地理和美术基础,算算、写写、画画、刻刻技能储备,被挖掘运用到了极致。使我终身难忘的是近距离接触了老杜。按照当时的时代语言,老杜是一个又红又专,不讲索取只是默默奉献革命的老黄牛。 到了1976年倪春,农田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毕,在辛寨党委班子鼓动下,全体农民开始投入进大战方田的施工阶段。 规划组的历史使命完结。 按徐书记的说法,我们是辛寨公社农业学大寨“方田”建设的参与者,功不可没。经徐书记极力推荐公社党委同意,给我们几人转成了老百姓非常羡慕的“亦工亦农”,分别进了几家在建中的社办企业,我以工程预算员的名义进了建筑队。 那个时候,我一个普通的农民社员与吃“国库粮”的老杜竟在一个办公室谋事三个多月。三个月时间在人生的长河中或许不长,我们从那分别后,又风风雨雨四十多年,各自忙于奔波,忙于求生,忙于事业,忙于婚姻家务,这一切的一切理由足以遮盖一度忘却,与老杜失联的理由和措辞。今日退休了,有点闲心怀怀旧,回忆经年,记录过去的时候,我才忽然想起一个最不该忘记的良师挚友——老杜。 我们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是纯粹的,纯洁的,毫无戒备的。请允许我用辛弃疾的《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为故事的结尾: 贤愚相去,算其间能几。差以毫厘缪千里。细思量义利,舜跖之分,孳孳者,等是鸡鸣而起。 味甘终易坏,岁晚还知,君子之交淡如水。一饷聚飞蚊,其响如雷,深自觉、昨非今是。羡安乐窝中泰和汤,更剧饮,无过半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