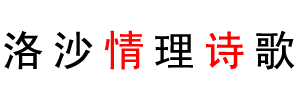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一转眼,四婶的三七就到了。 也就是说,四婶去世已经整整二十一天了。 老天爷也跟着伤心了二十一天,一天笑脸都没露过。 老娘却咳嗽快一个礼拜了,天天打着吊瓶,咳嗽却不见好。我心急如焚,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硬着头皮,遵照医嘱继续打吊瓶。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按说七天为一个疗程,明天再挂一天看看效果。 “二妈,好些了吗?” “二妈,我几个看你来了。” “二妈……” 四婶的三个女子提着各色礼品,看望老娘来了。娘屋子一下子显得狭小很多,气氛却温馨多了。 我手忙脚乱地端茶倒水,招呼客人们坐下。老娘与几个女子客套完之后,话题自然落到四婶身上,几个女子免不了哽咽半天,大家都缅怀起四婶的好来。 “唉,你妈比我年轻,才81岁,把我活多少是个够呀。”娘感叹起来。 “二妈,我妈没福,你要好好地活。有你们几个老人在,就是我们的福气啊。”姊妹三个轮流着给老娘宽心,一旁的我也轻波微澜,鼻子发酸,四婶生前的种种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眼前不断地闪现。 “二妈,我给你把饭端来了。”刚拔出针头,四婶的儿子新刚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烩菜走进屋子,烩菜上还盖了几个软蒸馍。 我们堂兄堂弟十人,新刚为九,我们就称他为老九。 “我爹说,第一碗给你二妈端过去。”九弟带来了四爸最质朴的嘱咐,“知道二妈不吃辣子,放辣子前就舀了一碗。”他又补充了一句。 父亲兄弟五人,娘妯娌五人。如今,十个人的团队已经去世了一半,现在就数老娘年龄大了。 新刚放下烩菜,就招呼他的姐姐们和我去他家吃饭,我以照顾老娘为由,婉拒了热心的九弟。 “太辣了,我吃不下去。”老娘吃了一口,就皱着眉头对我说,那副难受的模样就像吃了一把干辣椒似的。 “你吃去,我吃不了。”老娘把碗推到我的面前。 “里面没放辣椒呀,我不吃,你吃吧。”我又把碗推了回去。 “看起来不辣,吃起来辣的很。”老娘还是皱着眉头,好像刚吃的那一口辣劲还没过去似的。 我尝了一口,没尝出辣的味道。 “不辣呀。”我狐疑地推回了烩菜。 “你看,里面有椒颗。”老娘像发现新大陆般兴奋,笑眯眯地用筷子夹出一粒花椒。 “椒颗又麻又辣,我吃不了。”娘再次把碗推给了我。我瞬间明白了什么,鼻子一下子酸楚起来。 老娘年纪大,平日里常有亲戚朋友拿着补品前来看望,客人走后,娘就一一打开,然后说这个不喜欢吃,那个吃不了,全让我一个人吃。后来我就对她说,你不喜欢吃就别打开,她却依然打开,依然不吃,然后就逼着我吃完。说实话,有些礼品我也不喜欢吃。我不吃,娘就不高兴,我只好硬着头皮吃,娘就会欢天喜地的。 看着眼前被娘再次推了回来的烩菜,我的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五十年前的那一幕。 那年我五岁,一场春雨染绿了大地,河水潺潺地流,翠绿的柳枝迎风摇摆,葱绿的小麦度过了漫长的冬天,在春雨的浇灌下焕发出了新生翠绿,“咯吧咯吧”地开始舒展着身肢。雨水节气刚过,队长一声令下,男女社员统一春锄。那时候没有除草剂,全凭人工清理麦地里的杂草,每年要赶在麦苗“起身”(分蘖、拔节)前将地里的杂草清理干净,等麦苗“起身”后就不能再进麦地了,拔节后的麦苗枝既嫩又脆,一旦踩进去,很容易折断的。 社员在地头像天上的大雁似的,排成“一”字型,由队干部各带一支锄草队,分别在每一块田地里展开春锄活动。晚上回到队里的饲养室,由记工员给每一位社员记上当天劳动的工分,等到小麦收割归仓后,生产队根据挣的工分多少给农户分粮食。当时的男社员劳动一天是十分工,妇女七分。 娘和四婶她们被安排到生产队的山庄锄草。我提着小竹笼跟在后面,将她们锄掉的野草捡起,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娘再从我捡回的野草里捡出荠荠菜、勺勺菜、野小蒜等能吃的野菜,添补家里食用,不能吃的野草用来喂猪。锄地的妇女们大部分胸前挂一个布褡褡,有的系围裙,边锄草边捡野菜,队长发现后就大声呵斥、责骂。胆大的妇女根本不管队长的吆喝,发现可食的野菜后,就像群鸡抢食似的,一窝蜂地抢,因此,我捡来的基本上都是草多菜少。娘胆小,从来不敢捡,怕队长扣工分,每次散工后,才在苍茫的暮色里捡几把,然后拉着我急急地赶回家。 我们捡回来的野菜,被娘回家做高粱糊糊时,下到锅里吃。如果运气好,我就能捡到更多的野菜,娘会给全家人做菜疙瘩吃。在那个年月,二三月漫长的饥荒时期,全凭野菜添补度日。 中午时分,队上在山庄的窑洞里做一大锅麦仁(大麦去壳),给劳动的社员管一顿饭,大家纷纷拿出带来的碗筷排队舀饭。有的社员耍小聪明,拿来的饭碗比我的头都大,有人就讥笑,你的碗再大,灶夫的勺有数。队长规定,没参加劳动的人不管饭,我和小明、小凡一般大,长的都没有锄头高,当然没有资格吃队里的饭。娘领到饭后,就牵着我的小手,躲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去让我先吃,我却不愿意,非得要去人多的地方吃。娘哄着我说,“我娃乖,吃得饱饱的,个子长得高高的,长大了坐火车,开飞机。”我依然不吃,娘就耐心地用嘴吹着热气喂我,我一扭头,躲到了一边。这时候,小明、小凡两人各端一碗热气腾腾的麦仁坐到了我的身旁,“呲溜呲溜”地边喝边用一种优越的目光不时地瞟我一眼。我心里很不服气,他们也没干活,凭啥能领到饭吃?娘用自己的身子挡在我的面前说:“我娃乖,赶紧趁热喝。”我看了一眼碗里那清汤寡水的麦仁,哭喊着:“我也要吃一碗。”娘生气而又无奈地说:“我娃乖,你没劳动,队上不给吃呀。”“他俩也没劳动怎么就能吃?”我指了指旁边有滋有味吃饭的小明他俩。娘把我拽到一边,生气地小声说:“小明娘是妇联主任,小凡娘是妇女队长,你娘我是社员,咱能和人家比吗?”“反正我不管,我也要和他俩一样。”我任性地闹腾起来。“你这娃咋这么不懂事呢?”娘一边生气地责备我一边又要给我喂饭,我使着性子抬手一推,麦仁被我打翻在地,那红红的汤汁就像鲜血一样,慢慢地渗入到黄土地,一颗颗麦仁赤裸裸地躺在地上,睁大好奇的眼睛盯着幽蓝的天空。娘意外的没打我,而是坐到一旁伤心地哭了。 吃着碗里的烩菜,感受着老娘的温暖,泪水不由得“吧嗒吧嗒”地掉到了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