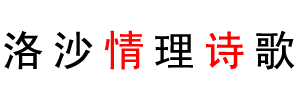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西部文学的敞开与照亮 文 | 杨光祖 西部文学内容厚实,历史感明显,有黄土般的品格,飘逸不足,但厚重有余。这也与西部这片土地的多灾多难有关。从《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我们可以读出历史的苍凉、民生的艰难和作家对底层人的同情和理解。《白鹿原》用50年的时间,写了50万字,这需要多大的才力?没有白鹿原的厚土,没有长安文化的积淀,陈忠实如何写得出这部巨著?伽达默尔说:“艺术的时间经验的本质就在于,我们学会了逗留。”《白鹿原》就是一部需要“逗留”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虽然有点单薄,叙事视角有点仰视,不乏权力崇拜迹象,但那种对底层奋斗的书写,还是感动了很多正在奋斗和曾经奋斗过的底层青年。 西部作家,一般多有情怀,生命体验深刻,有着献身文学的精神。这一点,陕西作家最明显。陈忠实自言,1986年,他清晰地听到生命的警钟。他想,如果写不出一本可以垫棺材做“枕头”的书,无法给自己、也给世人一个交代。路遥《人生》发表之后,忽然想到:“这一生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王国维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清代大画家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新的时代,有新的变化,文学的创作手法相应地也要有变化,否则无法真正书写出真实的新时代。我们读当年上海的新感觉派,他们的文学成就不是很大,但穆时英、刘呐鸥的小说,真的写出了上海滩的新面貌,包括舞场、跑马场等,那种蒙太奇的手法,是值得肯定的。我一直认为,中国现当代最大的先锋作家是鲁迅。我们一直说鲁迅是现实主义,其实不妥。他更多的应该是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他的小说有着强烈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色彩,《野草》就很明显。至于《故事新编》,就是中国最早的后现代主义文学。鲁迅在这里娴熟地使用了后现代技法,非常深刻地表达了他对时代、对社会的荒诞感和绝望感。 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必须在叙事上有所贡献,对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文学包括思想和形式两个方面,一个伟大的、独特的思想,肯定需要新的形式来表达。没有新的形式,也就没有新的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我们虽然人在西部,但我们的文学观念、艺术理念,必须是世界性的,要站在世界前列。否则,你的创作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最多就是一点地区性意义。 西部好多作家往往能创作出影响一时的文学作品,一瞬间照亮了某个角落,被全国文坛关注,但很快就湮灭于黑暗之中,甚至再无人提起。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一起被读者遗忘。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西部虽然面积上占了三分之二左右,但在全国文化地图中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所以,在这种观看和被观看的话语体系中,西部作家为了赢得关注,有时候就会产生迎合心态。按照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一部文学作品对它的读者的期待视野,会决定它的审美价值。他说:“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通俗或娱乐艺术作品的特点是,这种接受美学不需要视野的任何变化,根据流行的趣味标准,实现人们的期待。”西部作家的创作,很多就是如此,所以往往逃脱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他们写西部特有的文化符号,沙漠、戈壁、荒凉、落后,和敦煌、藏传佛教等等,其实,自己对这些文化也是知之不多,甚至完全陌生,只是在文字里玩弄这些符号而已。这样的作品,可以欺骗读者于一时,怎能流传于后世? 1857年,法国有两部小说,题材、主题、内容、结构都很相似,一部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部是他的朋友费多的《范妮》。福楼拜由于形式上的创新和“非人格叙事”而使读者寥寥,而《范妮》一年发行13版。但作为小说史上的转折点的《包法利夫人》最后获得了世界声誉,而《范妮》却成为了明日黄花。 西部作家大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的视野、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天然的局限性。真正的文学需要形式上的创新,只有作家的精神世界到达那个高度了,才可产生一种新的形式,才有一种创造新形式的冲动。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皆如此,鲁迅先生的小说也是一篇一个形式。他晚年的《故事新编》的特殊形式,是与他深广的精神世界有关的。 相比之下,西部很多作家其实还停留在题材写作的层次,停留在写什么的层次,也就是一种市场需求的层次,还没有走到追求自我精神诉求的层次。所以,他们的作品还只是一种暂时的畅销书而已。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这话是没有错的。伽达默尔说:“任何一件艺术品仿佛都为每一个感受它的人留有一个他得去填补的活动空间。”只有当你的内心是一重海洋时,你即便抛出几朵浪花,读者也能感觉到那种力量,那种气度。当你只是一洼池水时,你怎么翻腾,大家也无所畏惧。你要给你的作品留下一个让读者去“填补”的“活动空间”,首先,你得有那种巨大的精神能量。这就是西部作家努力的方向。 ——本文转自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