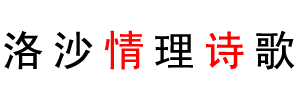菊花痴呆呆的坐在病房外走廊的长凳上,蓬乱的头发不规则的巻曲着,她刚打完点滴,用手压着针眼上的胶布静静的坐在凳子上。她盯人的眼神有点害怕,眸子里有一种抗争不服输的力量。
她是高考复读被学弟学妹讥笑长时间的抑郁而精神失常的,被父母送进精神卫生医院。送进医院的那一刻,母亲把女儿的头搂进怀里,泪水如泉涌一般,悲叹孩子后半生怎样度过。
母亲抽泣的胸膛让菊花抬起头,望着母亲流泪的眼睛,本能的用自己的右手沾了母亲的一滴泪水,放在自己的嘴边舔了一下,痴痴笑了笑,双手紧紧地搂着母亲柔弱的腰,久久不肯松去。
吃药打针天天如此,对已经麻木的菊花没有一点感觉,她无任何反抗的听医生的摆布。那些镇定剂、利眠药天天进入她的肌肤折服了她青春畅想的一切萌动。
走廊的两侧全是病房,时而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声,摔碎杯子的刺耳声,时而有大夫护士急促的跑步声。
菊花看着几位大夫跑步走进走廊出口处02病房,自己好奇的隔着门上小玻璃窗口看,几位大夫压着一青年,正在给青年的屁股打针。那青年很快就静静的入睡了,小时候曾看护士给自己的哥哥的屁股打针,她就用小手抓护士,拽护士的衣角。
菊花摇着头,噘着嘴看到了那一刻,就痴痴的坐在长凳上。打完针的菊花几乎天天如此。
通过这一幕触动了菊花的神经,菊花每天打完针都会扒在02病房的小玻璃窗口,向里张望,看到那青年卷曲的在睡觉,她不肯离去。
一天,菊花正在打吊瓶,又听见02病房那小伙子叫喊,她翻身下床,不顾一切的跑出自己的病房门,吊瓶架子被自己拉倒,吊瓶摔碎了,鲜红的血倒流出,她全然不顾,跑向02的房门,被大夫和护士拖回自己的病房。
02病房的小伙每一次叫喊,菊花就有感觉,好像相识,撕痛着菊花的心,她有一种萌动驱使着她,她不忍心那小伙子的尖叫,总想靠近他。这是两个互不认识、互不相干的病友。
打完针的菊花又坐在走廊的凳子上,在02病床的门上的玻璃口向里张望。
周六的下午,打完针的小伙子慢慢的走出病房门,护士在离他三米远的地方跟着他。小伙子在病区旁的花园里坐在石板凳上,仰起头,好像在寻找云里隐藏的星星。
菊花跟着小伙子的身影移动着脚步,看见护士她又退回来了。
一个病人的家属提着水果看望自己的亲人,那黄澄澄的香蕉勾住了菊花的眼睛,这是她最爱的一种水果,嫩黄的色彩让她激动不己,慢慢跟着陌生的家属进了病区。
阿姨!我要吃香蕉,菊花胆怯的喊了一声,两手不知所措,当这位阿姨转过身来,看见这是同类病号,痴痴的望着他提的水果袋子。
就从袋子里取出一把橡蕉,掰了一半给菊花,菊花忙摆手,从中掰下一支香蕉,把剩余的又还给了阿姨,转身拔腿就跑。
她跑出病区,透过走廊,能清晰的看见那个小伙子时,她停下了脚步,靠在走廊的柱子上呆呆的望着,看着小伙子坐在那里低着头,用脚在踢玩着一个小石子。
菊花靠在走廊的柱子上,盯着小伙子她停下了脚步,她很茫然,很胆怯,她萌生的意识中就想把这支香蕉送给他,愿他不再叫喊,不摔东西,不再痛苦。
精神的挫伤,让菊花的认知发生了障碍,一天脑子里就是混乱的,但是今天什么都没有想,就是盯着小伙子 ,一心想把香蕉送过去。他的心底开始升腾着一股炙热的关爱。
走过去,走过去,胆怯和勇气纠缠着自己,菊花终于迈开自己的双脚,径直朝小伙走去。
她突然坐在小伙子身旁,让小伙子下意识向旁边挪动了自己的身体,菊花眯着眼露出的善意,扒开香蕉皮,拉了一下小伙子胳膊,瞬间把香蕉递给小伙子。
小伙子突然感觉到一股温暖向他扑来,在家经常受到父母训斥,一天无路可逃,缺少关爱,缺少温暖,他冷漠孤僻的心把自己宅在房子里,用游戏消磨时光。菊花的举动,让他泪奔了。
小伙子用颤抖的手从香蕉上部掰了一小段,望着菊花善良的眼睛把剩余的多半支香蕉送给她,菊花却哭了,接过香蕉的那一瞬间,她感到世界上有人能瞧的起她,那往日的失落、白眼、讥讽此刻在他的心里显得那么渺小,在接到返回半支香蕉的那一刻荡然无存,她突然感到世界亮堂了,心里充满了阳光。
两个人吃完香蕉,静静的坐在哪里,望着前方几只麻雀自由自在的在嬉戏觅食,他(她)们似乎忘记了一切。
这一举动,让护士在长廊里看得清清楚楚,约莫半小时功夫,护士朝着她的方向拍着手喊,焦贵!回病房查体。焦贵飞快地站起来,向病房奔去,菊花望着他的背影,视线紧紧地盯着没有离开焦贵的背影,就在焦贵进入走廊踏上台阶的那一刻,他回过头来望着菊花,两只眼睛触碰在一起,片刻,焦贵返身跑回来,轻轻扶起菊花,两人痴痴相望,突然,焦贵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菊花,久久没有松开。
作 者 简 介: 吴康权 陕西临潼人,航空企业退休干部,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经济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未央作协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在报刊、网络发表散文诗歌百余篇,出版诗集《流韵》,短篇小说集《人生如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