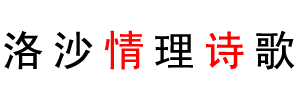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洛沙 于 2014-11-6 16:14 编辑
对吃最深刻的印象,是我跟妈妈住在一个叫三原的小县城里,从陕北来看望我们的舅舅扛着一麻袋土豆。那个月里,母亲把那一麻袋土豆,做成了几十种菜。煎炒烹炸拌,亏得母亲一双巧手,那一麻袋土豆变化成各种丝儿、片儿、块儿、面儿,进了我的小肚子。 这个月过去后,我见着土豆就想哭,直到现在对任何大品牌的土豆片都没兴趣,就算他们请了黄晓明或者周杰伦这样的帅哥做广告,我也不会多看它几眼。 土豆是妈妈家乡的特产,黄土遍地,黄沙满天,这种农作物倔强得跟当地人的性格一样,死死地在黄土地里生根发芽。到了收获的时候,它一定老老实实地在土地里成长成一窝拳头大小的果实,不知道救活了多少人命。妈妈常记起小时候,外公被打成“牛鬼蛇神”,一家老少的生活,要由妈妈——家里这个十二岁的唯一女性掌管。后窑里的一筐子土豆全部长了芽,妈妈舍不得扔掉,全部熬着给全家人分吃了。后来,她一想到这件事,就后悔的捶打着腿落泪。因为,外公、二舅、小舅最终都得了肝病,也都因为肝病相继去世,妈妈说,那是因为她把出了芽的土豆给家人吃,“是有毒的!” 上周杂志社有位尊贵的客人前来慰问,我们一同前往一家高档酒店。客人点了一道按位算价的菜,叫“三文鱼炆土豆”,一团粉黄色的土豆泥,因为加了高汤鲜汁而显得特别透亮。它,尊贵地被铺在三文鱼上,上面有一片翠绿的罗勒叶,鲜味扑鼻,色泽相当之——时尚。用小匙挑起一小块放进嘴里,真鲜呢,可是就是怎么吃都不像土豆。让人完全想不起它是全身被掩埋在黄土中,可以扔进快烧败的柴禾堆里,待熟后再扒拉出来,剥掉一层又黑又焦的皮儿,才能露出的又沙又香的瓤。 我常想,土豆如果是一个人,那它一定是女人,长得不漂亮的女人。就像我。但她有一颗美丽而丰富的心,她愿意把自己煎炒烹炖,样样都能滋补别人的身体。这点,我可不敢与它匹敌,我是自私的,小器的,我做不到一切都为别人着想。 大学同宿舍有个家在甘肃的死党,大学毕业留在西安考研,租了一间小屋,日日苦读。母亲去世后,打理完丧事,她一再要求下,某天我去她那间破屋看望她,她正蹲在单头煤气灶旁,一边搅着锅一边招呼我,说快开饭了。 我闻见一股熟悉但陌生的香味,进了屋。不一会,她端来一白瓷碗——是一碗鲜香的土豆沫糊。土豆蒸熟,压面,骨汤锅里慢慢打散,不停搅拌上劲,再将青色和红色的辣椒圈用热油爆香,泼进沫糊里,淋上香醋,口感幼细、酸辣可口。冷天里,我被辣的不住呵气,却忍不住吃了一碗,又盛了一碗。死党笑吟吟地站在一边看,一边递过来纸巾,让我擦汗。我知道,我吃了她的晚餐,就像小时候,常常因为爱吃某样东西,也吃了母亲的那份。但 我却吃得那么心安理得,那么理所应当。因为我知道,她是会高兴的,比她自己吃了还高兴。 热烫烫的眼泪,不自觉淌进碗里,伴着饭咽下。她也坐在一边抬手擦眼泪。说:“慢点,烫!” 千万别以为我死党就是个彻底的温柔女子,她倔得跟土豆一样。同宿舍的几个姐妹都结婚了,唯她因考研,一直没有男友。我着急上火,忙着介绍男友给她。终于,千万里挑上一个机电学博士,人长得也过得了眼。可约会才三次,就听男方说,“吹啦!”我忙电话问她,“怎么回事啊?”她不急不慢地说:“唉,人才啊!”我急急拷问下,才知。这位博士仁兄居然在用餐的时候说,“呀,这洋芋就是比土豆好吃!”相亲的另一位眼镜都快掉汤里了,小声问了一句:“那马铃薯如何?”博士仁兄朗声说:“噢!马铃薯比这两个都好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