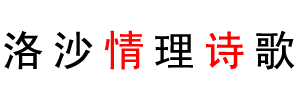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在家翻找一件小东西,无意中发现了一沓陈旧褶皱的票据单,顺手翻了几页,看见每页上面都写着妈妈的名字,仔细一看是在农村信用社存款的存单。一下子没了找东西的兴致,拿着存单去问妈妈,没想到却勾起了对过去的日子苦涩的回忆。 那一沓存单是妈妈过去十几年间积攒血汗钱的凭证。那些已经有点发黄的存单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和爸妈一起走过的平常日子。
妈妈半岁时就没了母亲,靠爷爷一个拉扯长大。为了不让妈妈受委屈,爷爷一直没有再娶,和妈妈相依为命,一辈子勤勤恳恳,节衣缩食。这样的经历和环境使得妈妈总觉得很孤单,特别是遇到什么事儿没有人帮衬,再苦再累都要靠自己,所以,从小就很要强。妈妈和爸爸结婚后,也只有我一个女儿,一家四口三代人,虽然也平平安安,和和美美,两代独女的生活总让妈妈去不掉心理上势单力薄的阴影。平常生活更加勤苦谨慎,开始还有爷爷帮衬照应,后来爷爷年龄大了,家里大小事都靠妈妈和爸爸。他们更是勤苦持家,能省尽省,总怕把日子过到人后头去。爸爸一辈子老实本分,没啥手艺,只有凭苦力吃饭。村子对面有几家石料厂,一年四季除了务弄地里的庄稼,爸爸大部分时间都在石料厂干活。开始是扛着铁锨去给拉石子的大汽车装车,装一车石子能分到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后来有了装载机,装车的活干不成了,爸爸又挖石头,从山崖里把大块的石头挖出来,打成小块再运到碎石机跟前。几十年来,就这样靠着地里种的棉花、玉米之类经济作物微薄的收入,和爸爸干活挣的钱, 家里的日子算不上富裕,也勉强过得去。
1999年,八十多岁的爷爷不幸去世,加上之前我也结婚成家。连续经历的这两次大事,在我们这里的农村,没有两三万元是拿不下来的。爸爸妈妈攒下的那一点积蓄哪里招的住这般折腾!从那以后,爸爸更是狠了命的在石场干活。几年后,石场因为环境问题大多关停了,爸爸就到周边的村里干建筑活。妈妈更是一天到黑都在地里忙活,棉花、玉米、花椒、豆子、黄花菜,一年四季只要能挣钱的都种。家里一直都养牛,前多年纯粹是为了农活。因为我们村地处河沟,地都在沟坡地带,机械化耕作不方便,耕种、施肥、收获拉运都要靠牲畜。这几年,不种麦子了,许多农事都是拖拉机完成,好多人家都不养牛了,但是,爸妈还一直养着一头牛,不为别的,就是一年能挣个卖牛钱。其实,卖牛挣的是整钱,但是平常割草打料拉出拉进,花的料钱、费的功夫哪个不是付出的零钱?但是爸妈不嫌那个麻烦,不怕那种劳累,门前院落总是摆满了新割的或者晒干的饲草。算起这种账来,妈妈总是说,农村人就是务农,不动弹哪来的钱,功夫还能算钱?
妈妈就是把她和爸爸用自以为不值钱的功夫和苦累换来的钱,一点一点积攒着,稍微有点数额,就存到信用社去,生怕放在家里,让平常柴米油盐之类琐碎的事情花掉了。翻翻那些存单,大部分都是五六百元一张的,能攒到一千元的很少,还有几张是三百元的。妈妈是多么想攒够一千元再去存啊,但是,一千元攒起来太难了,她只能那样几百元几百元地攒存。我大约数了一下那一沓存单,时间主要集中在1999年和2003年前后,大部分是存在信用社在村里设的信用站,只有几张是乡信用社开具的,一共有四十多张存单,加起来总共才两万多元。
看着那一张张存单,我似乎看见机器轰鸣的轧石场上,爸爸满头是汗,把一车石块艰难地推向轧石机。到处是沙堆和砖垛的建筑工地上,爸爸从砖垛上抱下一摞砖,向正在加高的一堵墙走去,砖摞的太多了,一直摞到他的下巴,他不得不仰着头,慢慢地走。我又仿佛看见,烈日下的棉花地里,妈妈弯着腰,正在一个一个地掐棉花树上的顶芽。晚霞余晖里,妈妈手里牵着牛,背上扛着一大捆青草,踯躅在村子下面的小河边。村后那条熟悉的坡道上,寒风嗖嗖,爸爸和妈妈拉着一架子车土粪,妈妈在前面牵着拉车的牛,爸爸驾着车辕,因为是上坡,他的身体向前倾着,和地面差不多成60度,嘴里呼出的热气里寒冷的空气里立即变成一团淡淡的白雾······
看我在那儿认真地翻看着那些存单,妈妈说:“那都没用了,我放在那儿都忘了,去烧了吧。” 我本来还没有什么意识和打算,一听到那个“烧”字,我忽然激灵了一下,赶紧把那些存单整理了一下,紧紧捏在手里。我要把它们好好保存起来。
我庆幸,岁月难留,却留下了见证爸妈艰难岁月的这一沓存单,它们就是爸妈汗水的结晶,就是爸妈留下的传家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