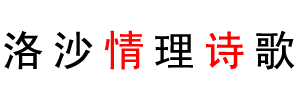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雪儿 文/幽谷罗兰 一 初次看到雪儿,是五年前的初冬。 身材臃肿的柳嬷嬷半拥半揽,将一个羞怯的少女推进了我的美容工作室。看着嬷嬷对那女孩的谄媚笑脸,我误以为那女孩是她的亲生女儿。 嬷嬷是一家茶楼的老板娘,她常常带着那些满身风尘味的姑娘们来做美容。舒舒服服地躺在美容床上,敷上面膜,姑娘们便开始露骨地切磋勾人法术,嬷嬷也毫无避讳地把茶楼男客们的私情当做谈资,来消磨敷面膜的漫长时光。在她们的言谈之间,我读懂了茶楼的真正生意经,因此当嬷嬷突然带来这样一位清纯的女孩,总会令人产生误会。 嬷嬷说她是新来的茶楼服务员,叫雪儿。 她让我给雪儿配些能增加肌肤光泽的草药面膜。看着那张稚嫩白皙的脸,心里突然五味杂陈。 雪儿每天来做面膜,嬷嬷总是寸步不离,仿佛看着自己的宝贝。雪儿很少讲话,总是羞怯地听着嬷嬷絮絮叨叨地讲,哪位姑娘被哪位老板包养了,哪位老板给哪位姑娘买了新楼。听着这些,心里总是替雪儿忧虑。 嫩肤面膜第一个疗程结束的那天,嬷嬷有事没有来,雪儿自己来了。我趁机试探着雪儿,“你想不想学一门手艺,将来自己做老板?” 雪儿微笑着说:“如果能拿出学手艺的钱,家里就不会让我辍学了。” “我不收你的学费,你肯不肯来我这里做学徒?” “谢谢你了,姐姐。我明白你的好意,家里的弟弟要读书,父亲又病重,我不得不早点赚钱养家糊口,学手艺的事,只能以后再说了。”她眼角的面膜浸出湿痕。 “如果你需要钱,学徒时我也可以按月给你薪酬。”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她拖出泥潭。 “姐啊,现在我想逃都逃不掉了,嬷嬷家的司机在楼下等着我呢。为了给我爸付医疗费,我已经欠了嬷嬷十多万元钱。如果不还完钱就离开茶楼,嬷嬷不但不会放过我,反而会牵连到你的。”她脸上的面膜被眼角溢出的泪水冲散。 无奈地送走了雪儿,我的心里好像扎了一根刺在隐隐作痛。 二 雪儿再次出现在美容工作室时,是第二年的初夏。 一股烟酒掺杂劣质香水的风尘味道,随着她的身体袅袅地飘进来。 “姐姐,不记得我啦?我是雪儿。嬷嬷有事脱不开身,让我来帮她买瓶晚霜。” 我努力从她微笑的眉眼里寻找,怎么都找不到初见她时的一丝模样。那张庸脂俗粉的脸和金黄的披肩卷发,总是无法让人联想到初见时那个羞涩清纯的少女。 不知道是该惊讶时间的无情,还是该惊骇人的善变,短短数月,能让一个纯洁的少女,完全蜕变成另外一个,不便使用更恰当的言词来形容的女人。 无奈地打发走雪儿,我的心里仿佛被一团莫名的东西堵着。 三 再次见到雪儿是两年后的夏季。 家里宴请远客,因为人太多,就临时决定去步行街那家新开的云水阁酒楼订了个容纳二十人的豪华包间。 酒宴快要结束时,我看到对门雅间的门口,蹲着一个妙龄女孩。她正在逗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玩。为了躲避包间里的浓重烟酒味道,我找个去洗手间的借口,起身来到走廊。那个学步的小孩子像只摇摆的小企鹅,竟然咯咯笑着向我扑过来。 “姐姐,你还那么漂亮,皮肤还是那么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雪儿。”妙龄女孩抬起头惊喜地看着我。 “雪儿,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惊讶地看着她。她浓密的黑发松散地挽在脑后,毫无修饰的脸,散发出一种自然成熟的魅力。从她简洁的妆容上可以判定,她已经离开茶楼了。 “是不是已经离开茶楼了?”悄悄地问她。 “是,离开很久了。”她的脸突然绯红。 “你还小呢,应该考虑学一门手艺,将来可以安身立命。毕竟不能永远给别人打工。”心里由衷为雪儿能离开茶楼而感到高兴。 “谢谢姐,一直在心里感激姐,却没有机会回报。我下去让厨房做两个菜,赠送给姐姐。”她抱起孩子。 “真的不用了,客人们已经快要散席了。你的收入也不多,还是留着供你弟弟上学吧,……” 没等我说完,雪儿笑着说:“姐姐,这是我开的酒楼,你就别客气了。” “这个宝宝也是你的吗?”我有些惊讶。 “是,已经快两岁了。” 她抱着孩子下楼了,看着她单薄的背影,我突然窘迫的不知所措,内心升起一种莫名的酸楚。 四 最后一次看到雪儿,是去年的深冬。 那一天雪下的特别大,茶楼的嬷嬷急匆匆地敲门进来,冰冷着脸,身上带着袭人的寒气。 “妹妹,给我准备够一年使用的化妆品和面膜,我让司机下午来取。” “姐要出远门吗?”我问。 “嗯,去外地旅游。”她走到窗前神色不安地向外张望。 “不用下午,我这里还有存货,再多配些面膜,你稍等会儿就可以了。” “好,你赶紧给我准备吧。”她趴在窗台上依旧向窗外注视。 “楼下有什么热闹吗?”我好奇地问。 “出这么大的事,你不知道啊?你快来看,抬出来了。” 我凑到窗前向窗外看。楼下对面洗浴会馆的门前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旁边停着两辆警车。几个警察抬着一副蒙着白色床单的担架向白色救护车走过去。 “有人溺水了吗?”我紧张地问。 “傻妹妹,那么浅的洗浴池子能淹死人吗?她肯定是被人弄死的。活该!她就是不知好歹,包养她的国局长被抓起来后,我找过她,让她回茶楼,她不同意。” “姐说的是谁呢?” “雪儿。” “啊?雪儿?她不是开了个酒楼吗?” “是啊,哪酒楼是国局长帮她开的。国局长因为贪污被抓,酒楼也被查封了。他的老婆找人把雪儿打了一顿,把她所有的积蓄和首饰都收走了,然后把她和孩子赶出了家门。为了养活孩子,她就去洗浴会馆了。” 我想再看一眼雪儿,但我什么也看不清。纷纷扬扬的白雪,白色的床单,一切都被白色掩盖着。 在白雪的映衬下,我只看到一缕长长的黑发,像蔓草一样在担架的一端无力地随风飘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