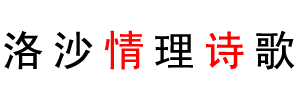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人间烟火 于 2015-8-12 09:47 编辑
小时候,村子里有一段时间流传一个类似算卦的手抄小册页,把生辰年月等信息和里面的条款对照,就能预测出你的性格、运气和前途命运。现在想来,那无非是玩儿的东西,但是当时我们几个玩伴竟对那小册页上的谶语深信不疑。更侥幸的是,按照我的条件,小册页上预测我将来能成为文学家。那时候对“文学家”一词,仅限于课本上毛泽东评价鲁迅先生 “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提到的“文学家”概念,并不知其真正的含义,只是朦胧地知道那是个了不起的称谓。那时从学校到村子里,人们都认为我字写得好,于是同伴们就更加认定小册子上的预测是千真万确的。玩耍的时候,时不时就说我是未来的文学家之类的话,同伴中一个稍年长的竟然因此对我有了一点妒意,好像我已经是了不起的文学家了,尽管比他小。 遗憾的是,从小学到中学,尽管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读,经常参加各类作文比赛,但是我始终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行当是写文字,写得好就能发表,印成书。直到高中时,有一次,几个同学闲聊,谈到当时广播里连播的小说《人生》,其中一个同学不但对那个小说很熟悉,而且谈到了作者路遥。我才意识到小说,包括各种文章都是人写出来的,并没有自己原以为的那么天造地设的神秘。此后多年,特别是上师专之后,在学业、工作之余,我一直断断续续地写些孤芳自赏的文字,偶尔向一些报刊投稿,不敢说心存所谓的文学梦想,纯粹是兴趣。可惜的是,无论是怎样的想法,除了收到过一两封退稿信外,所有的想法都是妄想。书并不是谁想写就能写的,文章也不是谁想发表就能发表的。理想和现实原来竟这么遥远。 1994年,我的第一篇“豆腐块”终于登上了《渭南报》,当时在师专上学,没有收到样报,是一位乡党同学不知在哪儿看到后,路上见了我顺便向我证实的。那也算是我人生诸多第一次中的一个,也是我梦寐以求的第一次,心里的激动就像圈在笼子里的鸟儿扑棱着翅膀,总想往出飞。尽管只是地市级党报,但也使我对写东西信心大增。到第二年师专毕业时,《渭南日报》已发表了我十几篇文章。我非常感谢这十几篇文章,使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的我,历经曲折最终找到了一份至少有机会舞弄文字的工作。 记得有位作家说过,“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我随心所欲的写写划划,是断然称不上文学的。即便如此,也许是工作和生活相对稳定消磨了让我潜意识里一种动力,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后来在机关搞文字工作后,由于疏懒,以及观察力的局限等等因素,除了工作范畴的讲话材料,文章写的越来越少了。几个月写不出一篇,或者写了发表不了,渐渐地越发懈怠。有时心里有写的冲动,迟迟动不了笔,冲动就慢慢淡化了,所谓的灵感也消散了。似乎不写了吧,偶尔又提起笔,甚或发表一次,写吧,又是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种写东西的状态,让我想起过去在家里务农浇地时水流的样子。水在坑坑洼洼的庄稼地里漫流着,地势低时流的快点,地势高或者遇到土坷垃时流的慢些,只要不疏浚引导,它就那样在地里漫无目的地流,也不管那儿的庄稼浇透了,那儿还没浇到。我觉得,这种水流的状态就是我这多年来断断续续写作的状态。 这几年,不再在文字工作岗位了,不用绞尽脑汁地写行政材料了,散文写得多了。过去的同事说,材料写了几年,你还没写够啊?我立刻纠正,写散文与写行政材料完全是两码事。写材料是用自己的手写别人想说的话,是揣摩着写,跟演戏差不多。写散文,才是我手写我心,写的是自身感悟,是心灵体验,是真正的言为心声,做人就是做文,做文就是做人。就这样,虽然也是断断续续的写,但是积少成多,几年来,加上以前写的文章,积累下来也有二三十多万字,一部分还在报刊杂志得到发表。这使我对庄稼地里的水有了一种更深的认识。水流在庄稼地里,有一种非常谦卑,扎实认真的态度。水流在庄稼地里遇到坑洼,不管大的还是小的,不管深的还是浅的,它总是先流进坑里,慢慢地把坑溢满,再溢流到另外一个坑里或者是庄稼苗的周围。每次浇地时,我喜欢专注地看水在地里漫流的样子。我觉得正是水这样谦卑扎实的态度,才使得整个庄稼地的土壤和庄稼得到滋润,才有了丰收和果实。写作也应该像庄稼地里的水一样,一丝不苟地流淌,一丝不苟地滋润每一寸土地、每一株庄稼。写作也应该以谦卑的态度对待文学经典,学习文学经典,从经典里吸收营养,获得知识和能力。以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文字,甚至一个标点,写好每一篇文章。 也正是这样谦卑地写作,认真地耕耘文字,我的写作没有什么成就,但也值得欣慰。前年我把过去十多年写的文章,精心挑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浅流漫迹》,得到市作协的关注和好评。去年有一篇散文《乡村里那一缕炊烟》参加首届中外散文邀请赛,还获得了一等奖。今年,随笔《从布鞋到皮鞋》在西部文学网举办的征文中又获得优秀奖。虽然算不上什么成就,但是,每每翻阅既往的文字,在孤芳自赏的同时,那些粗拙的文字总是把我带回过去的时光,就好像有一个另外的自己,从时光深处走来和自己对话和交流,有时候甚至会惊讶,曾经的我怎么能迸发出那样的心灵火花。这样的感觉比任何的获奖都来得实惠,来得令人快乐和慰籍。 也许这一生成不了作家,更不会像小时候游戏预测的那样成为文学家,但是,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一种精神支柱,就像流水那样,不求闻达、没有目标,却谦卑而认真地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