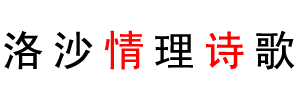古风情韵的老街
在享誉中外的石刻之乡——大足,自成渝高速公路和成渝铁路交汇处的邮亭镇,向东去两里许,有一高坡名叫“五里堆”。站在坡顶上远眺,周边儿青青的巴岳山脉逶迤起伏,足下圆溜溜的山丘莲花般四散开去,衔接了远山。那山底的沟谷,白色的公路蜿蜒其间,而老街,则一如蛇般从沟谷向上游移,静静地盘卧在了五里堆坡的半山腰。
顺着沟谷的公路至上,一踏上青石板铺就的街面,浓浓的乡情就如水漾开了我颤动不已的心房:哦,老街,你依旧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旧模样!
只是那青色的条石,却没了当初尖利的棱,看上去细腻、柔滑,中间一条浅浅的凹道,在阳光下,泛出些微的银光来,它们一块紧衔一块,密密地、曲曲地,延伸过去,不像近处高速公路那般张扬、豪放,而是给人一种宁静和从容的感觉。
街道很窄,两三米余宽。两边的青瓦房呈“一”字排开,颇有气势。壁墙多用褐色的木板串架而成,历经风雨的侵蚀,早失去了昔日华丽的色彩,不过却显出另一种厚重而朴实的美来。
赶集日,当街而过,阳光下,没有声息,早不见了当初摩肩接踵的赶集人。屋檐下,几个老太太玩着纸牌,几个老大爷呷着茶水。他们埋怨说,姑娘嫁走了,儿女买房到附近的邮亭车站,孙子们不愿意到老街来耍了。耄耋之年的杨保元老人敲打着手里的秤盘,一声叹息:祖祖辈辈都是做秤的,独生子却放弃了家传祖业,跑买卖出去了。
唯一让老人们高兴的是,古朴自然的老街,今年春吸引了法国的朋友们来参观,武汉建筑学院的一群学生也背着画夹兴致勃勃而来,在此写生了一个星期。
如果华年的流逝吞食了这已老了的老街,那我坚信,老街的风采,已留在了那群风华正茂的学生们的画册中,并被装帧成一幅最精美的风情画,长久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心灵深处的文昌宫
伫立坡顶俯瞰,见一石梯弯弯曲曲,逐级而下。视野尽头是一口清清的水塘,脑海里立时便涌现出它旁边的文昌宫的模样。
文昌宫位于老街正中那株大黄桷树下,一座极普通的建筑物,但那却是老街几代人的精神家园。至上世纪90年代初,无论是镇上中小学校放电影、节日演出,还是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看戏,都在此处。
如果要看戏,需要从正街,穿过一幽深的小巷,踩过湿漉漉的布满青苔的地面,便至文昌宫的后门入口处。门口通常由两个表情很严肃的人把守,观众大多很自豪地高举手中好不容易得来的票,把门人颔首,他们便兴奋地挤进小门。进得门后,虽然室内地面是凹凸不平的,人群也挤得密不透风,但大人小孩却都很兴奋,眼睛只盯那舞台。那舞台用木板搭建而成,两侧有梯。台正中立一挡板,作演员化妆用。
那时候一般演的都是川剧的某个片段。我第一次看川剧的时间大约在6、7岁,母亲赶完集就牵着我的手走进了文昌宫。那时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真不知道生活中的场景要怎么样才能在那小小的舞台上表现出来呢?还依稀记得:红布帘缓缓拉开,当着戏服的女演员甩开长长的衣袖,迈着细细的碎步袅袅婷婷地走进舞台正中,开始“咿呀咿呀”地唱时,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循着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我走进了文昌宫,心里却伤感不已:墙垣已倾颓,舞台也失却旧日模样,只有几根桩子,在孤零零地诉说着它曾拥有的辉煌。我便想,也许,老街的人,是把它深埋在心底了,慢慢地欣赏着它、咀嚼着它。
傲然挺拔的黄桷树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这方土地,默默地为老街挡风蔽日的,是那六七棵枝繁叶茂的黄桷树。
站在街中仰望,每一棵树都是那么挺拔、魁伟。仿佛持枪的勇士般,威风凛凛、英气逼人。它们拥有一样粗壮的干,苍劲的枝,以及那一汪油油的嫩绿叶片。但是,每一棵树又各具情态,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自己的美。
位于街头的两株黄桷树,属重庆市二级保护树木。右边的那棵紧傍一住户,根部全裸露在近3米高的乱石堆上。近看那根,或粗或细,或曲或直,须脉毕现,溢出一缕鲜活的生命力。宛如蛟龙,盘缠在一起,在嬉戏,在飞腾。据户主介绍,这根有的便如剑般刺过了墙壁,在其厨房内蔓延。
右边的黄桷树根部用石栏围住,青色的树干便暴露无遗。上面斑痕累累、裂纹道道,一如淌过岁月的长河。两棵树在空中相拥,一副水乳交融的样子。
让人称奇的是那几株市一级保护树,雄踞街中文昌宫上的黄桷树,宛如大力神般,张开巨臂,欲揽小街入怀,其绿荫覆盖十余米外,气势颇恢弘壮观,直逼霄汉。根深植于沃土之内,干突然中分,盘曲而上。绿绿的青苔粉饰了它的颜色,袅袅乐音在我的心中回响: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这是叶对根、树对街、树对人的情呵。树下劳作的80高龄的陈老说,儿时在它的怀里嬉戏,饥荒时曾摘它的叶充饥,她也在树下长大成人,树装饰了她一生的梦境。
昂立于老观音堂处的一级保护树,树根全裸,棱角分明,造型各异,似假山堆砌而成,最底部却鼎足而三,呈镂空状,轻敲发闷闷的声音。树干正中,赫然显出一深洞。老人们说这洞以前曾住一观音,慈眉善目,佑一方水土,这地方因此而得名。
夕阳西坠,走过老街,走过古树,心中涌生的恋情如水弥漫我心房。只愿这山更青,树更秀,无论小街的人走到何处,都如树般屹立在他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