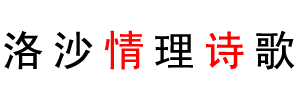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闭上眼,时光流逝,忙碌的蚂蚁被人摘下触角,和我一样在空旷的岁月里流浪。 “来,喝一杯酒。”这是一句没有太多激情,平淡如水的话,他总是喜欢这样。 “不,我不喝酒,我只喜欢自己的茶。”对于酒,我已经厌倦,不管怎么说,那些我自己回忆起来都尴尬的日子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比如斗殴,说是斗殴其实是被人结实的揍了一顿,比如在那泛起涟漪的湖水边舞动青峰,说是舞动,其实我知道那是我在借助青峰躲避着自己内心的灰暗,还有些什么我没有说到?我记不起来。 我没有喝酒,只是静静的坐在他的对面,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只是平淡,却如同天际那抹云霞,他的瑰丽让你想到一种永恒的美丽。 “那么你喝茶,我喝酒,我不喜欢勉强别人。”他还是那样平淡如水,不给你激情,不给你哀伤,只是永远那样淙淙的在你的心底流淌,那是山泉吧,我记得自己曾经在那乱石和松树之间闭目,在半睡半醒之间,那一曲天籁是怎样让自己忘掉尘世的,那是山泉的天籁之音。 我喝着茶,几案旁的茶树开着大朵大朵的红茶花,即使是这样冷漠的冬季,那些茶花也傲然的将自己的青翠和大红迎着金风,将一切的腐朽恣意的嘲笑,我喜欢这样的喝茶,无拘无束,即使对面的人喝着的是酒,然而茶会冷,酒不会,所以我的茶总是被沸腾的开水浇淋,他的酒就少了这许多的繁琐,倒入杯中,抬起自顾自的倒入喉管,吞咽,我很难说是酒好喝还是茶好喝。 许多的话放在心底,他不说,我也不说,可是我们都知道,或者我们都在等,等着他的酒醉,等着我不安于那茶盏的静寂,也许我们都渴望旁边那一棵需要数人才能合抱的大树跌落的树叶,渴望那树叶落在杯里,然后才可以有相谈的话资。 “还有那么多的叶子可以掉落啊。”树叶跌落在酒杯里,他抬眼看看那一树枯萎的叶,感叹着。 “是啊,这树叶其实不脏,很干净,比来这里的路上那些有着厚厚脂粉的女人干净,比那些在车里望着那些女人的男人干净,至少没有艾滋病,没有性病。”我站起身,将他杯里的那片落叶捡起,轻轻的放在带着茶色的玻璃之上。 “你是劝我和她分开吗?你和她上床了吗?”他很平淡的问,很像不是关于自己的问题。 “是。”我的茶带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带着涤净一切的清泉,却让天际的白云总是摆不脱被风卷刮的命运,茶的命运注定成为我的血液或者尿液,我的命运则注定我将成为伤害另外一个或者几个人的命运,“即使我不和她上床,她也会和别人上床。” “呵呵,即使这杯茶不是你喝也得有人喝,对吗?”他缅缅的笑着道。 “是啊,我喝了。”我不知道该笑或者该怎么样,对这样一个男人,或者什么话都很多余,或者我该说说她,或者说说那一个茶杯。“杯子要有茶或者酒才能够醉人,好的杯子是不会被人空着的,女人也一样。” “是啊,我们已经半年没有上床,一年没有牵手,日子很淡,我不知道自己得到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失去什么,不过我知道她会偷偷对着电脑笑。”他给自己喝空的杯子又斟满酒,“你觉得你能够给她什么?让她永远满满的?” “也许不能。”我很坦白的说,因为我的确不能。“但是我可以让杯子永远装着液体,或者眼泪,或者欢笑,或者是什么也好,我不喜欢让一个非常好的杯子空着。” 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于是十年过去,还是在那一个茶几的旁边,还是一杯酒一杯茶,不过喝酒的人是我,喝茶的不是,是另外一个可以让茶杯茶香盈盈的男人,当然不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