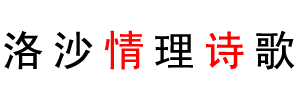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
乌江号子(外二章)
石头的花朵,骨血的声音,灵魂的呓语,陷入时空的苍茫。 “脚蹬石头手扒沙,咳咗!”上滩号子的吼起,上水船在一寸一寸地挪。苍穹下,云深雾浓。 “弯腰驼背把船拉,咳咗!”纤夫的脚步,撵着乌江的涛声一步一步地移。云彩是帆,船在梦的深处。 “一步一躬一把泪,咳咗!”热辣辣的太阳挂在了山上,湿漉漉的憧憬挂在了山上。一只岩鹰,盘在九天之上。 “恨不能把天地砸,咳咗!”把铁齿铜牙般的风雨踩在了地上,把龙骨石般的人生踩在了地上,一条石旮旯的纤道,一条生生不息的活路。 “清风吹来凉悠悠,咳咳!”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喊起,晃荡的心,追撵着激荡的流水,捏一把劲道十足的惬意。 “连手推船下涪州,咳咳!”梦想赶着热望,挺拔一生不变的祈求,憧憬的潮浪在心头卷涌。孩子的鼻息在梦中响起,一盏摇曳的桐油灯,亮到了天明。 “有钱人在家中坐,咳咳!”人心不静,浪也难平。梦想的碎片,抓紧了,就从指缝间滑落,放松了,仍在指尖上闪烁。 “哪知穷人忧和愁,咳咳!”阳光熄灭之后,乌江大峡谷是一处甘露的圣坛。 炫耀在大峡谷的生命之光,在激越的号子中穿越了时空……
古盐道
吃滚滚盐,什么味道?土地爷晓得。
吃望望盐,什么味道?老天爷晓得。 仁岸、綦岸、涪岸、永岸,乌江四大口岸血脉喷张。 生命的盐粒爬行在古老的盐道上,一匹矮脚马迎风嘶鸣。 大风在刮,黑云的手帕擦不干太阳的泪水。 挑盐巴去了,贵州、云南闪烁着四川盐井的白。
盐布包,在汤水里滚了,轻轻的一漾,又一漾,赶紧提起……滚滚盐,斗米斤盐。
悬块盐,在房梁上裹了,仰起头来,嘴里的饭菜入盐入味……望望盐,一眼晶莹。
一群在乌江血盆里淘命的人。纤索直,稳。船头翘,沉。纤索,拉紧梦想的鳞片。
一群在盐大路上吃血饭的人。山罩雨,停。江罩晴,行。雾罩,网住期望的羽毛。
挑盐巴去了。母亲,回答询问父亲的儿子。 挑盐巴去了。儿媳,回答追问父亲的儿子。 挑盐巴去了。婆婆,回答探问爷爷的孙子…… 一句流传了几千年的话,泪湿了乌江岸边黝黑的龙骨石。
“吆来哟,吆哦……”盐船纤夫,吼喊的狂嗓溅落了历史的烟尘。
“嗬哟嘿,嗬嘿……”盐道马帮,吆喝的长啸沉寂了大山的呼吸。 乌江的古盐道,龙骨石睁亮乌黑的眼睛。 民生,这两个字,从古到今都滴着鲜血。
哭 嫁
乌江姑娘,在闺房里晃动绯红的心事。 哭,一种与生命同在的等待,一种悲和喜的表达,一种命与运的倾诉……一顶花轿,其实花轿有时也可以忽略。 哭别老屋里的自己,田野中的自己,父母姊妹心头的自己,邻里眼中的自己。 哭别用过的镰刀、锄头、斗笠、蓑衣,鸡、狗、牛、羊、猪以及树稍的鸟雀…… 从此铺开一条山高水远、烟笼云卷的路,一条悲悲喜喜、生生死死的路,一条只有怀思不能重复的路。哭嫁,更有了分量。 姓氏就这样淡化在哭声里,哭声袅袅在炊烟里,炊烟浮动在乌江号子里。 一场哭嫁,把乌江姑娘哭成了乌江女人。发芽,抽穗,扬花,结籽。号子开枝,哭嫁散叶。 千里乌江把哭嫁的歌谣一遍又一遍的揉洗,清透了汗息,通透了心扉。 坚韧的心音,煌煌猎猎。这不是一场盛宴之后的错觉。 孕育的光芒,瞩望的泪眼,在乌江大峡谷之上,舒卷着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