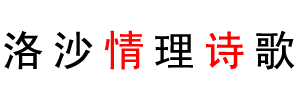在丹江南岸,有一片依丹江而展开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田,人们把这里叫做百顷湾。我的外婆就住在百顷湾的河涧村,和丹凤县城一江之隔。
小时,外婆家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每当母亲带我去外婆家时,我就会高兴的一晚上睡不着觉。那时的丹江上没有固定的桥,而丹江水却很大,夏天可以行船。丹凤县城南有座花庙,是船帮会址,也是船工歇脚的地方。我和母亲夏天回外婆家,要坐摆渡船过丹江。深秋后,过的是临时搭建的木板桥,走在桥上,看到脚下湍急的流水,总是紧紧拉着母亲,怕掉到江里。
过了丹江,不远处有一座水磨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路过那里,总能听到江水打在水轮上的“哗哗”声和水轮带着磨子运转时的“咯咯吱吱”声。从水磨坊到外婆家,也就一两里路,路两边全是稻田,稻花开时,远远都能闻到清清的香味。有时晚上到外婆家,路上行人很少,静静的。深秋季节,皓皓月光洒在路两边收割后的水田里,泛起一片片银色。江边的风,吹在空中的电话线上,像是在摆弄提琴上的琴弦,“嗡嗡”的响着。而水田里的青蛙也不甘寂寞,在“嗡嗡”琴弦声的伴奏中,你一声、他一声,“呱呱”的叫个不停,似乎是一场音乐会。不时能听到青蛙从地垄上跳到水田里的“扑通”声,这一瞬间,“呱呱”的蛙叫声就会戛然而止。也就是又一瞬间,一片蛙叫声又再响起。
到了外婆家的河涧村,一道引丹江水的堰渠穿村而过,清澈的渠水流出村子,流向那百顷水田。村里人洗衣、洗菜,都用的是渠水。而渠里常常能看到泡着的木头,似乎也没人担心会被偷去。外婆家就在离村边几十米处,有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院子。院子中间,是用河卵石铺成的路,由东朝西,通向外婆住的上房,又分了个叉,通向北侧的厨房。院子西南处,有一口井,很旺的井水,冬天的井口总是浮绕着水气,周围的邻居都吃这口井的水。东南角的篱笆里,一株株月季花姹紫嫣红的开遍时,给外婆家带来一片生机。而院墙内外几棵核桃树,大大的树冠,每年都能收到满柜的核桃。
每当东边天角抹来一缕阳光时,伴随着家家户户的鸡叫声,外婆和外爷就出了屋门,先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听到“咯吱”一声,打开了院门。 不一会儿,前来打水的左邻右舍就在一声声问候声中,三三两两挑着水桶进了院里。这时,望眼村里,袅袅炊烟,扭动着柔软的身姿,悠悠然然地飘向远处的天空。不远处,在牛群“哞哞“的叫声中,夹杂着放牛人的吆喝声。这一切,仿佛都在告诉人们新的一天田园生活的开始。
有时早早起来的我,在院里着急,就会跑到村东边的水田看外爷做农活。百顷水田上空,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人在地边,就如身置仙境一般。而外爷和一起做活的农民老大爷、农民伯伯一样,身处仙境不知仙,一点也没有那神仙的潇洒,只是一年又一年辛勤的劳作,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额头上,就像刚犁过的田地。只有在看到滚滚稻浪时,他们的喜悦才展现出来。
记忆中的百顷湾,总是那般令人陶醉。而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外婆的善良、外婆对我这个唯一的外孙的疼爱,还有和舅舅家表妹、表弟在一起的俩小无猜,都常常在脑海中浮起。如今,外婆去世已四十六年,母亲也已寻她而去,但我还不时回到百顷湾,回到河涧村,看我的舅舅和舅妈。每当我看到外婆院里的那口井,看到还挺着身子的核桃树,听到“咯吱”的开院门声时,外婆那爽朗的笑声和从眼神里流淌出来的关爱,就又在我眼前掠过。
而这时的百顷湾,却早已没有了过去田园风光的宁静和美好,多了不少现代社会的浮躁。丹江的水小了,看上去就像一道小河沟,没有了江的气势。那座水磨坊也没了踪影。路两边的水田已成为旱地,不规则地散布着家户住房和间隔在其中的小商店、歌厅,各种车辆扬着尘土行驶在路上。穿村而过的堰渠已被填平。百顷湾没有了水,也就变成了百顷“弯”。